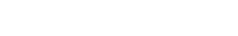在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上,“五道口”已经成了专有名词,专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30年前,198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挂帅,由属下金融研究所出面创办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四大银行:工、农、中、建,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参与创立和教学。之后,它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这是中国当代教育史上最小的研究生院:1981年第一届招生18人,第二届22人,第三届23人。几十名学生,加几位教学管理、后勤人员,没有专职教授,却是“成才率”最高的学院。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一个五道口现象:五道口的毕业生,形成了一个对中国金融资源、财富、机构整体性影响的群体。仅就一所学校形成网络,对历史产生影响的现象而言,五道口并不独特。比如,美国有哈佛大学,中国有清华大学,民国有政治大学等,然而,像五道口这样体积小、能量大、历史短、膨胀快,转动资源大者独一无二。
2011年9月23日,在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五道口纪念它的30岁生日。在很多道口人心里,这场纪念,与其说是庆生,不如说是告别。历史在这里定格,——五道口被并入清华大学。
应运而生
1981年,中国的金融改革不仅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全面启动。与农村改革、企业改革比较,金融改革的困难尤其明显:
首先,没有参照系。1949年以前,中国虽然是二元经济,金融货币经济却相当发达,与世界同步。中国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创建国,拥有现代银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一流的银行家、金融家。即使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金融业也没有中断。但是,经过计划经济时代,1949年以前的金融体系,回不去了;前苏联比中国迟缓,没有多少参考价值;西方无法复制。中国必须另辟蹊径。其次,没有足够的思想理论资源;第三,人才匮乏。尤其缺乏立即可以派上用场的新型金融人才:思想解放、知识结构新、热衷改革、年轻。问题严重啊!在上述三大困难中,人才无疑最重要。然而,人才哪里来?无非是三种选择:
第一,依赖现有高校。且不说远水解不了近渴,数量也不够。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的研究生名额只有10个。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1930年生)向系主任黄达要名额。黄达(1925年生)给了他两条建议:第一,不要依靠人民大学,学校名额有限;第二,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考虑成立自己培养研究生的单位。话说回来,即使黄达满足了刘鸿儒又怎么样?也只是杯水车薪。人民银行需要“定向”培养,充实“干部”。
第二,发扬“革命”传统,建立速成班,培训班。这种办法对于培养现代金融人才完全不适用。此时,自1977年恢复高考过去四年,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过去三年。中国建立了研究生培养制度,国家学位委员会呼之欲出。“文革”期间粗糙的、工农兵学员的时代统统俱往矣。
第三,创办新型学校,培养“子弟兵”。刘鸿儒代表了那一代先知先觉者。他们决心自己培养,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真有“创业”精神。面对历史造成的人才断裂,没有非常办法、速度和精神,无法逾越。五道口,是逼出来的!
为解燃眉之急,却成为改变金融环境的一个支点,这是五道口创办人和1980年代最早投奔五道口的学生,始料未及的。中国从非货币经济到货币经济,从非金融时代进入金融时代,他们参与其中,担负重要角色,是天赐良机,时势造英雄。
自由、开放、务实
审视五道口的足迹,可以看到自由、开放、务实其实是它不成文、没有铭刻在墙上的校训。得以凝结出这样的精神,其基础条件是:
首先,思想资源丰富。没有陈旧的教学模式,不囿于一家,才得以开放,兼收并蓄。五道口在全国范围内挑选老师上课、办讲座。在北京,除了聘请北大、人大、中央财大的老师,也请清华老师教授数学、化学、日语。山西财经学院的金融史比较强,就请来那里的孔祥毅;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哪位老师好,也请过来授课。此外,连临时出差来中国的外国专家也不放过。第一位做讲座的外国人是纽约证券交所主席凡尔霖(JohnJ.Phelan),时间是1986年。在破旧的教室里,学生竟然用英文跟他谈刚发生的“金融大爆炸”话题,令凡尔霖吃惊。在之后的邓小平接见中,他对邓小平说:“你们的年轻人很厉害。”五道口是中国最早开设资本市场课程的。参与建校的黄永鉴老师一语道破:“没有老师,可以聘请到最好的老师,因为我们不受师资编制限制。靠着总行这棵大树,我们找谁谁都答应。”
其次,与实践结合。各银行行长、司长皆为兼职老师,甚至导师。他们把现实问题带到课堂上,理论和实践直接碰撞。学生一步跨入改革前沿,师生共同研讨国家金融发展战略。唐旭(1983级)对刘鸿儒的课印象最深。1978年刘鸿儒出任农行副行长,之后回人民银行任副行长。他所参与的改革,经常作为案例在五道口研讨,包括农村金融改革、人民银行与工商银行分家、人行独立行使央行职能等,并围绕这些改革组织各种研讨会,银行界、理论界的都来。这些,给学生带来难以想象的刺激和激情。
第三,试验探索精神。据王巍(1982级)回忆,很多老师来上课,一进教室,先跟同学说,“这是一门全新的课,是一种尝试,所以心情是战战兢兢的,希望与大家一起讨论”。比如厉以宁说,“过去没讲过这个课,是为了你们花了几个月心血准备的”。有一次,他在课上讲一个问题,学生波涛不同意,说:“厉老师,这个你说错了”。厉以宁一听,真怀疑自己错了,就按学生说的改正。可是,第二天再来上课时,他说昨天讲的没错。于是,重新讨论。王巍说“这种拿老师当朋友,彼此很平等,共同探讨的学术精神使我铭记一辈子”。厉以宁的好几本书,比如《经济学面临的挑战》,都是在五道口的讲义基础上编辑成书的。程博明(1984级)还记得,五道口老师讲课经常不从教材第一页开始,可能一上来先讲第76页,再讲第20页,最后又跳到130页。不照本宣科,看上去全打乱了。考试时,学生都把教材扔到一边,主要阅读笔记。这提高了五道口学生的思维能力。
第四,和国际接轨。人行金融研究所有不少民国时期留学英美的学生,空怀报国之志,一生受压,赶上改革开放,已进入老年。他们有良好的教养和修养,积数十年研究思考,倾注巨大热情,全心全意向年轻一代传授知识。他们中英文俱佳,讲正宗的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等等。在西方经济学专业被冠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的时代,五道口得天独厚。
今天看起来当年那些劣势:仓促上马、没经验、没师资,恰恰转化成为五道口不拘一格的特色和优势。因为没有师资,而引来丰厚的师资;因为没有教材,而传授新鲜、带有探索性的成果;因为没有繁琐的教务系统,而施行扁平管理,师生亲密。一个学校的风气和时代的风气连在一起。人们多赞赏和珍惜1980年代的五道口精神。万建华(1982级)称之为:开放性、实践性和多元化。
文武之道
学校的名望,常常取决于学生。
五道口1981级和1982级研究生,多是老三届,经历过上山下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80年代初是崇尚理工,追求文学,流行朦胧诗的时代。多数人参与农村和工业改革,普遍对银行知之甚少,更不懂股票、债券,想象不出不久的将来,保险会成为大产业。而这批人,则选择了银行、货币、保险这些冷门专业,表现出超前意识。报考经济类,金融类,特别是五道口的研究生,没有教材可供准备,没有导师的著作可以参考。程博明说:五道口和其他院校不同,每年的考题都没有固定模式和内容,甚至没有固定课程,复习都不知道该重点看什么。他自己以阅览杂志作为考研的复习方式,比如,为英语看《北京周报》,为专业课看《经济研究》一类杂志。
唐旭说:那时在五道口,有人会一夜一夜不睡觉讨论改革问题,也有人会熬夜读英文。从五道口创立就在这里讲了30年数学基础课的北大教授秦宛顺、靳云汇夫妇对武捷思(1982级硕士)印象深刻。武捷思读博士时已经在中国工商银行任计划资金司主任:“他一旦出差缺了课,缺多少,下了班就到我们家里补课。每次来都端一个很大的茶叶杯,三分之二都是茶叶。因为工作一天很辛苦,为了不犯困,用浓茶提神。确实很不容易。”
除了刻苦,还有理想和执着。让五道口名声大噪的是1981级和1982级十几位同学于1984年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上发布的金融蓝皮书,关于中国金融改革战略。它第一次突破和计划经济体制和银行控制的框架。他们坐火车赶去合肥,不是受邀代表,不能上会,住在会场外农民办的家庭小旅馆,一门心思,志在上大会发言。蔡重直(1981级)跟黄达说,您让我们发言,我们发言;您不让我们发言,我们也要发言,您哪天开完会我们就哪天上去说。黄达听了笑了。最终,大会给了蔡重直15分钟。那天,十几个同学进入会场,三个人上台宣读金融改革“蓝皮书”。蔡重直形容当时的场景:“会场很安静,仿佛有一股清新的风吹进来。”发完言他们集体离场。想不到被媒体疯狂追问。不久,中国银行主持的中国国际金融年会开始对他们的主张进行批判:“这是搞资本主义,还要在中国重开证券交易所,不是回到旧中国了吗?”平时严厉的黄永鉴老师,私下建议蔡重直先躲一躲,不要来学校。过了一两个月看看没什么大事,蔡重直们“又开始折腾”。
理性和野性,成熟和顽皮,既在大事儿上较真,又不拘小节,他们身上都有。有一天,在黄达老师课上,张志平(1981级)呼呼大睡。因为教室供暖不足,他带了床棉被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黄永鉴老师看见了,一状吿到张志平父亲那儿。那是位严父,回头就踢了张志平一脚。对此,张志平不仅不记恨黄老师,反而对他尊敬有加。五道口北边院墙和东升乡政府共用一道墙。校门关了,他们就翻墙。既登堂入室纵横国家大事,又夜里翻墙课堂睡觉捂被子。这,就是那批学生的本色!
怎么评说?
五道口创造了辉煌,特别是1980年代毕业生,发起并参与创办了诸多中国第一,包括证券公司、股份制银行、上市银行、基金、民间最大信用社、柜员制银行、企业并购公会、金融博物馆等等。沉浮兴衰,大风大浪。
五道口的“老三届”(1981、1982、1983级),入学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如今普遍进入花甲之年,有的已经“退休”。他们恰巧经历了中国金融界30年的天翻地覆,成为弄潮儿。30年,是一代人。历史眷顾道口人,将他们的事业成功和制度充迁与时代发展重叠在一起,他们是幸运的,值得骄傲,也被同代人羡慕。然而,还不仅如此。
首先,它是历史机遇。在中国诸多改革中,金融改革包含着一系列制度性的重大变革,从而提供了巨大的舞台。很多道口人都十分清醒。比如万建华说:“我们的机遇很好,每班车都赶上了。”夏斌说:最初几届的不少同学被推向领导岗位,重要的原因是机遇好,当时人才青黄不接,需要一批西方经济学、金融学背景的人才,我们正好赶上了。而黄永鉴始终强调五道口的最大特色——人民银行背景。作为中央银行的嫡系、子弟兵,可以捷足先登。
其次,是金融经济的整体膨胀。过去30年,金融资源经历了甚至是从零到无限大的过程。以商业银行为例,金融资产膨胀的规模远远高于GDP。最早接受现代金融教育,进入金融领域的人,自然随着这个球体的膨胀而发达。
再次,金融关乎国计民生。它是达官显贵和市井小民关心的重心;物价指数、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则是媒体焦点;1997、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汇率、股市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举足轻重。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核心成了金融。“货币战争”、金融安全,警钟长鸣。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各个领域人才辈出,不乏所谓的精英和佼佼者,但是,五道口这个群体最引人注目。因为它集资源、权力、财富、影响力于一身。王巍说,从五道口毕业的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闻名于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的“精英圈子”。黄永鉴说,五道口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比较特殊。随着毕业生越来越多,圈子逐渐扩大。他指出有一种“强大的向心力”。这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原本中国有很多金融人才,特别是民国时期。然而,历史一次次断裂。可以说,是历史的遗憾反衬出了今天的辉煌,辉煌背后是时代的悲剧。在正常的社会进程中,不会有这样的历史机会。
问题是,五道口现象不可持续。如今,金融改革日常化,金融资源膨胀时代大体完结,金融人才从短缺变为“过剩”。五道口现象所代表的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时间推移,五道口的先天缺陷开始全面显现。最为理性的声音来自厉以宁。他认为五道口在学术上没有做出应有的成就,是因为三个原因:一是没有专门的教师队伍,好的教授都是外聘的;二是受专业局限,只懂金融;三是缺乏综合性大学的学习资源和学术氛围。他说,外聘教师的模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可以用,但创办五年以后就应该为长远着想,逐步培养自己的教师队伍。再有,“大学要去行政化,而五道口的管理是行政化的”。前几届,各高校的优秀学生都往五道口考,北大、人大的一大批教授前往授课,造就了五道口的辉煌。然而,后来五道口的教学质量和生源质量,有下降趋势。
对于五道口并入清华,道口人反应不同。有遗憾,有无奈。有一种意见认为那样的话,研究生部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没有优势、没有特色”。而所谓优势是指央行的背景。也就是说,这种主张是:宁可接受五道口停办,也不同意它脱离央行与高校合并。
黄埔军校并没有持续下去,抗日军政大学也没有持续下去。为中国金融改革培养急需人才、“火线培训”而创办的五道口,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虽然有遗憾,但是不能不看到,大环境、小环境其实都过去了。应运而生,历史在此定格,未必需要伤感。理性地说,五道口以这种方式结束是一个自然现象。
三十年五道口,有骄傲,也有遗憾;有满足,也有自省;有荣耀,也有教训。“五道口”是中国现代金融史上的里程碑,上面记载着一个独特的、绝无仅有的五道口现象。(文中道口人谈话内容,来自《与中国金融改革同行——五道口30校友访谈录》,《当代金融家》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