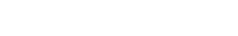入学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至今,一眨眼二十一年已过去,今天五道口校友办工作人员发来秦宛顺老师和靳云汇老师的照片,一时间感触莫名。
(一)
一九九四年,带着某种并非正直学人所应该有的功利,考入五道口攻读博士学位。在上个世纪,五道口的教学一直保持两大特色之,一是学术讲座较多,有人民银行总行和各商业银行总行实践与学术兼顾型领导,也有大量的外国访问学者。二是研究生部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老师,授课老师大多来自北京大学,秦宛顺、靳云汇夫妇每到一节课快要结束的时候,秦老师就会把钟拿起来,以高度近视者特有的方式,把电子钟拿起来放在离自己眼睛较近距离地方看时间。当然也有中央党校、外交学院等,而秦老师和靳老师就是其中两位。
开学后的第一学期属于基础理论教学阶段,秦宛顺老师给我们讲授的课程是《高级微观经济学》,这在五道口博士研究生教学大纲中,属于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每一次讲完课,秦老师都会给我们布置作业,而这些作业大多是与当天所讲经济理论内容有关的一些数学推导或证明。我们一个班共七个学生,数我年纪最大,加之在上大学前,只在乡下上过几天人民公社革委会领导下的初级中学,所以,对于每一次秦老师布置的作业,其他同学一般都在晚上九点钟不到就做完了,可是,我却要到深夜十一点后才能勉强做完。
上课的时候,尽管我们班七个同学中,除我之外的大多数同学都能顺利完成秦老师布置的作业,但是,仍然会在一些关键计算上,尤其是微积分及矩阵推导经济理论结论的过程中,出现一些理解上的困难,所以,同学们一般都会在第二次上课时,针对上一次作业的一些数学推导向秦老师提问。五道口所有的学生都知道,秦老师有较为典型的高度近视,很多时候是无法远距离判断提问的学生是谁的,于是就会走下讲台,拿过提问同学的作业本,将眼镜脱下,几乎是鼻尖贴着作业本那样近的距离,检查提问同学的求证过程,看完了,秦老师把眼镜戴上,然后重新回到讲台上,用他那仍然带着浓重河南口音的语调对同学们说:“这个问题很容易证明”。
后来,秦老师的这句话,成了我们七个同学回答彼此之间一切提问的经典话语。只要我们互相问问题,无论是不是数学求证的问题,回答问题的同学都会学着秦老师的语调,善意调侃一句:“这个问题很容易证明”。
由于我的数学底子太差,上秦老师的课对我来说,并不像其他同学那么轻松,每一次交到秦老师那里的作业,当秦老师第二周批改回来的时候,我都会发现在一些关键推导和计算的地方,会有密密麻麻的红笔修改。
对于秦老师的课,还有一件记得较清楚的事是秦老师不用手表,而更多是要看钟来查阅时间的,秦老师每次上课,都会拧着一个当时老师这个行业较为通行的手提式布袋包,在这个包里其实只有两样东西,一是秦老师要用的教科书,二是一个小钟。秦老师一走进课堂,就会将这个钟放在桌子,五道口那时并没有统一指示上下课的铃声。所有的老师都是自己掌握时间,所以,每到一节课快要结束的时候,秦老师就会把钟拿起来,以高度近视者特有的方式,把电子钟拿起来放在离自己眼睛较近距离地方看时间。
根据教学安排,大约是在第二个学年的上半个学期,秦老师的夫人靳云汇老师来给我们上《计量经济学》课程。对于我来说,这门课和上秦老师的课,有着同样的难度,每次听靳老师讲课完了后,我对有些较为复杂的计算和推导过程总是无法彻底弄明白,所以,几乎每一次上课,我都会抓住课间时间拿着课堂笔记去问靳老师。但是,无论我怎么努力地听和向靳老师请教问,毕竟自己的高等数学底子太差,最后仍然是在似懂非懂中上完了靳老师的课。到了期末,需要通过本课程考试,靳老师要求大家自己搜集宏观金融数据或经济学数据样本,自己做一个回归案例。
那时候,数学分析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做回归分析并不是在Window视窗系统下,由一个EXCEL文档软件就可以完成的,而是在DOS系统下由一个专门的TSP分析软件来实现,这个TSP软件是由DOS指令来实现,尽管靳老师上课的时候反复讲解每一个操作指令的含义,以及如何依据步骤输入操作指令,我自己也在笔记本上将每一个操作指令的含义都记了下来,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自己仍然会犯迷糊出错。
到了要交考试卷的时候了,由于数学计算缺陷,自己对自己所选的样本和回归操作仍然没有把握,于是想到要将自己所做的回归分析拿到靳老师那里请她先给看看,给评一评,指导一下。
可我并不知道秦老师和靳老师家住哪里,于是请了比我高一届的学长帮忙,由他带我去靳老师家。走进较陈旧的老师宿舍区,徒步爬上了三楼(大概是),进了靳老师家,那天正好秦老师也在,看了看秦老师和靳老师的住宅,面积并不宽,估量了一下,建筑面积最大不过九十平米,家里设施也比较简陋,与那个年代的一般国民家庭比,没有什么区别。
受我邀请与我同去的学长坐下与秦老师交谈,我则抓紧时间将我的回归分析报告交给靳老师,同时说了我对这个回归及相关检验不能把握的地方,靳老师针对我的计算步骤,一步一步地帮我推导和计算,并在每一步骤上面都做了批注,同时也做了关于这些地方未能做准确的原因讲解。大约花了半个小时,靳老师给我讲解和在作业本上做了批注,于是和秦老师、靳老师道别。
下到楼下,出于担心,赶紧把经过靳老师批注的回归分析报告给了学长看,结果,这位学长直截了当的学告诉我:“你这个回归几乎就是不成功的,或者可以说是全盘没有意义的。”听了学长这一番话,尽管多少有些为回归分析报告不成功而懊恼,但这仍然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是惊叹靳老师竟然拿出如此大的耐性给我把整个回归分析报告讲完,而且还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进行批注修改。在当时,是无法从“师道”之伟大,去深刻理解靳老师如此诲人不倦的精神的。
到了自己也成为一介大学老师,才开始体会像秦老师和靳老师他们这一代“真的学者”和“真的师者”品格之伟大。我现在共带有六名研究生,每一年要给两个班的研究生上课,以我带的研究生为例,当发现他们不能很快发现自己的知识兴趣点和专业领域取向,不能以比别人更强的毅力刻苦读书时,我就会在每一次与同学见面时,使用最为严厉的语言面对他们,有时,甚至可能是有损他们自尊心的。每每当我把最严厉甚至可能是有伤学生自尊的话说完,时过不久,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有些内疚的。今天当写到秦、靳二位老师的为师之道,那样高尚的诲人之诚,自己多少会觉得惭愧的,惭愧原因并不在于能不能给下一代学者以世俗繁华追求方面的帮助和支持,而在于不能给予和告知他们正直和具有韧劲的文化人品格。
(二)
2005年,自己因为深感与工作环境不适,于是离开了具有高薪待遇的国有银行总行,去了边境省份的一所大学当老师。无独有偶的是,就在我所去这个大学任教的第三年,即2007年,悉知每一年国内第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都会面对国内其他大学招收访问学者或进修教师。其实,无论访问学者还是进修教师,也就是在教育部组织之下,一些国内二流大学到国内知名大学作教学培训。在北大光华学院的辅导老师中,赫然看到秦宛顺老师的名字,于是赶紧向我所在的学校提出申请,并报在秦老师名下,这个报名得到了学校的批准,当然也得到了秦老师的同意。开学的前一天,跟秦老师联系上,决定去秦老师家看一下秦老师和靳老师。
秦老师一家终于搬离了那个陈旧窄小的居室,在清华东路这边一个相对像样的小区的五楼,有了一个相对大的居室。按响门铃,是秦老师开的门,靳老师那天正好有课,不在家。扫了一眼感觉秦老师这个新的家,装修得还可以,远不是十年前的那个居室可以比拟,但是,同时也有了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感觉,那就是:秦老师已不再像十年前那样显得年轻了,这一年,秦老师已经七十一岁,一切都当然不能再与十年前相比了。
我原以为秦老师已经不再上课了,可是,我在北大光华学院本科生课表上,还是看到了秦老师的课程安排,而且还在研究生课表中看到了靳云汇老师的课程安排,于是,决定去听两位老师的课。秦老师的课都是安排在早上,所以,我得起早从家里开车去北大,努力争取自己不要迟到。作为访问学者,尽管这并不是必须要遵守的事项,但是,作为一份自我约束,自然包含着对秦老师的尊敬之情。
秦老师还是那样,拧着一个口袋走进教室并径直走上讲台,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圆形钟放在讲台上。应该坚信,整个教室除了我以外,这些我在北大的临时“同学”,他们应该都是第一次上秦老师的课,所以,当秦老师第一次上课把钟拿出来的瞬间,有一部分同学情不自禁地“啊”出了声音。整个听课期间都很平静,不过有一件事还是值得一说的。开学后不久的一次课,秦老师正在黑板上书写那些他已经铭记于大脑的数学推导公式,突然,下面有学生的手机铃响了,秦老师停下在黑板上的书写,走下讲台,在两排课桌中间的通道上,走了一遍,由于他眼睛高度近似,实际他也看不到什么,只是问了一句:“是谁的手机响了?”
学生们一片沉默。
秦老师并没有说什么,然后又回到讲台继续在黑板上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书写他的数学推导过程。
我很惊奇,秦老师居然一句责怪和批评的话都没有说。当然,这以后似乎就真的再没有学生的手机在课堂上响铃了。
就在那个学期,我还听了靳老师给研究生上的《计量经济学》课程,在那个100 人的大教室里,虽然没有手机电话铃声,但是却不断地有学生走出大教室去打电话,靳老师似乎觉得这一切都属于研究生课堂的一种必然要素,并没有对学生们这种稍显随意地在教室里外往返提出任何质疑和批评。
可能也就是因为听了秦老师和靳老师课,才使得我学会了如何适应已浮华而不可逆的世界,这种“适应”,当然也就包括了“师道”之“严”与“慈”的客观综合。于是,在后来我任教的那个大学,只要是我给研究生上课,我就会做这样的约定:同学们有事,可以到教室外去打电话,但课堂上手机必须放在静音上,不能在教室响铃声,这就是基于研究生比本科生具有更强的自制能力而确定的一种妥协。
有绝对的道理吗?没有任何一个大学老师可以对此加以肯定,但是对于我的内心而言,我相信:这种约定来自于我在上了秦老师和靳老师的课以后,于是产生了一种职业借鉴和反应。
(三)
2009 年,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第二次去北大光华学院做访问学者,仍然报名在秦宛顺老师的名下。到学校后,问清楚秦老师的课程安排,在老师休息室里见了秦老师一面。这一次秦老师直接就对我说:“小侯,这个学期你不一定要听课了,自己研究点东西吧”。
“好,秦老师”。毫无思想准备之下作了简短答应。自知这一次去北大作访问学者,在情理上是讲不通的,毕竟在我任教的那个大学,甚至可能很多大学都不会连续两次让同一个老师去同一个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之所以能够再次到北大光华学院,并且继续在秦老师名下辅导,除了一些自己世俗原因外,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一份情感。在北大光华学院期间,也听了张维迎老师(院长)的课,课的内容听进去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1988 年从西南财大到五道口听课时,就曾经就听过当时刚刚从海外回国的张维迎老师的课,再一次听课,时过境迁,于是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无独有偶的是,好像秦老师就知道我这次回来再做访问学者,而且再次报在他名下某种特殊心情一样,居然在第一次见面就针对性地给我明确了一个宽松的学习过程。到了2010 年要结束访学的时候,我向北京大学培训部交了一篇研究论文,论文题目是《经济学庸俗化的伦理考证》,按照规定我要提交给我的辅导老师秦老师签字。秦老师在论文上做了签注,而且给了很高的评价,而且还推荐到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专刊》,获得当期北大访学学术研究成果三等奖。于是,在秦老师大度而精心地安排下,这样一次访学顺利结束。
(四)
每每回忆在五道口、在北大光华学院听秦老师和靳老师课所积下的点点滴滴珍贵记忆,尤其是我在北大光华学院与二位老师有了超出于五道口范围的师生之谊,终可以理解什么是“真师,真道”。
秦老师和靳老师都是学数学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搞市场经济的起点上,需要在理论上重新学习以古典经济学为发端而形成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可是,像一个整体还处在托马斯·阿奎那政治文明阶段的社会,要在短时间内接受所谓托马斯·潘恩政治文明设计一样,我们的西方经济学引进,从一开始就面临了数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应有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秦老师和靳老师从数学转向了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
记得奥地利籍经济学家冯·哈耶克1956 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大楼启用25 周年纪念大会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我们每个人在自己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里,大概都是靠十分年轻时得到的观念而生活的,但是,对于数学家或逻辑学家来说,这意味着他在18 岁便做出辉煌的成果,而作为另一个极端的历史学家,有可能80 学才能成就其最好作品”。
这段话是冯·哈耶克在讨论所谓“无机复杂性”和“有机复杂性”,并以此比较物理、数学等数理科学与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在获得成功方面艰难程度差别而说的一段话。我相信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话,其实就是学术领域的现实。所以,对于秦老师和靳老师他们从一个数学领域的学者,转而从事经济学教育,也就预示着他们走了一条比之初始专业更艰难的学者之路,可是,社会和我们的历史发展,需要他们这一代学者有人来做这种不计个人成功的选择。
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知识分子的智慧与良知被利所绑架的事例比比皆是,而同样,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义愤而不满于身处局限,乃至企以大声嘶喊却又无以真正抒发胸积的人,也是随处可感。而像秦宛顺、靳云汇两位老师那样,一生秉承教书育人、克己淡利,坚守学人品德的师者,可能就不是太多了,尤其是面对浮华尽显的世界,他们那种可以不被任何非正道伦理所刻意偏颇的师者品格,却并不是每一个文化人都能做到的,这应该就是整个社会都应该对之那严肃然的“真师者,真师道”。
侯合心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日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