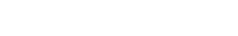温和儒雅的唐旭以一种学术良知和坚韧的意志力,在商业大潮中守住了连一些著名高校都频频退却的防线,他因此获得了大家发自内心的尊敬。
得知唐旭生病是两年前,兄弟们很震惊,相约去看他,然而传来信息说,他需要静养;得知唐旭病重是半年以前,我出差去上海,用了半天时间,带着兄弟们的嘱托,在沪郊松江一个理疗院里看到他,人瘦削了一圈,病象很重。一个始终善良微笑着的唐旭,一个烟酒不沾生活健康的唐旭,竟然被肺病折磨成这样!相见半分钟,我俩忍着,说不出话来。情绪镇静之后,我们愉快地交谈了一个半小时,谈过去,谈身体,谈朋友。我珍惜这次的相见,因为半年之后,即2011年1月28日他去世前3天,我和王承远、张凤鸣兄在301医院看到他时,他已失去了语言(包括肢体语言)表达的能力,从英国赶回来的女儿拉着他的手。我们痛楚地感觉到,这个人间终于难以留住大家所敬重的唐旭兄了!
我和唐旭有同乡同窗双重友谊。论年龄他长我8岁,当他在四川乐山青衣江畔当纤夫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因此,不能体会他早年的苦辛;恢复高考后,他于1979年进入西南财大,我则是1980级学生,师兄师弟在母校的校园里并不熟识。然而,他的勤奋,特别是他考上“五道口”研究生部的事迹,却令我们很钦佩。后来,陆续看到他写的一些文章、编著的货币银行学书籍。师友们聚到一起总要问一问,“唐旭最近又写什么了?”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金融界的青年学者中,唐旭不算是最活跃的,然而,他无疑是最踏实和最有定力的学者之一。鲜有惊人的言语,多是扎实的工作,在金融教学、研究、域外金融论著的译介这些基础性工作层面,唐旭做出了默默的奉献。因而,对于后学者,他的教益更广泛,影响亦持久。
大潮中守住了连一些著名高校都频频退却的防线,他因此获得了大家发自内心的尊敬。那时,我所供职的银行正在进行初期的业务结构调整,中国人民银行也在酝酿改革信贷规模管理,号召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管理。“不能光做信贷,要多买国债,又安全收益又高!”他对我说。我担任总经理的计划资金部负责全行计划、流动性、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唐旭兄的这些意见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那几年,我们这家规模不大的银行多次成为债券主承销商、副主承销商,固定收益颇丰。在2003~2007年我因工作关系辗转于云南、深圳期间,唐旭兄来开会或路过时,总要争取见上一面,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很关心,情景恍如昨日。
唐旭任职任教五道口研究生部二十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学生,他无疑是一个优秀的教员;后来他又做了人总行研究局局长、反洗钱局局长,应该算是金融高级官员。在教员中,他的官位是比较高的;在官员中,他的理论水平是比较高的。然而“两员”之间,他更像一个具有传统人文情怀的教员。在京城的川渝兄弟时常聚会,大都有些豪爽的气质,在杯盘交错、热气腾腾之中享受着同乡同窗的情谊。唐旭是兄长,有空必定参加,然而他总是温和而安静。大家对他称“唐兄”或“唐校长”(当了局长之后也是这样),言谈中较少问他“某某事该怎么办?”更多是问他“某某问题该怎么看?”可见,大家也是倾向于视他为教员的。
唐旭走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承受着“数人少一人”的痛楚。在2011年2月12日送别他的悲痛时刻,上千人的队列中,我和童频、任道德、郭晖、凤鸣、承远等兄弟在一起。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细读着人民银行印发的“唐旭同志生平”,其中记述了他早年做过纤夫的经历。是的,他始终是个纤夫,他不仅是川江上的纤夫,更是中国金融界一名勤劳的纤夫!
当我于1997年4月从上海来到北京工作时,唐旭已担任五道口研究生部主任职务。多年不见,他拉我去城郊春游,倾谈一日。谈起五道口,他滔滔不绝。“一定要守住,至少硕士生这个环节不能搞在职读!”在接过前辈创业的旗帜之后,唐旭恪守了起码的学术和教育规则,聚天下英才于五道口,使之成为金融学子向往的重镇。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金融界的青年学者中,唐旭不算是最活跃的,然而,他无疑是最踏实和最有定力的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