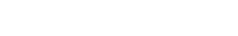此文已新浪原创上首发

二、同学·相识
在大学的时候,我和唐旭都是属于社会青年考进大学的那个群体,与应届考起的同学比,我们所具有的特性就是:都不再是少年。
大学的四年,我和唐旭不在一个班,但是,由于学校是一九七八年才刚刚恢复招生,学校一切硬件设施均还处于恢复之中。我们入学后最初那一学年,金融系一个年级大约九十个男生,几乎都住在被我们命名为“老黄楼”的底层,整个年级男生的寝室,分布在一个平面“7”字型的底楼楼层里,我和唐旭算是同住在“7”字的长把一边。
我们这个年级,是介于七八级和八零级之间多少有些特殊的年级。在七八级,一个班里几乎全是社会青年考入的,所以,大家除了年龄会有一点纯数字上的差距外,认识和思想的成熟度应该是相对均衡的。而八零级呢,虽然仍然有一部分社会青年考生考入,但由于应届高中毕业生占比已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整个年级的同学关系特性更多表现为高中时代学生情感的延续。
只有七九级,社会青年考生与应届考生之间的对比相对均衡,社会青年考生略高一些,学校也可能就是出于应对这样一种特殊年龄结构的考虑,对每一个寝室里的学生安排,在年龄上进行了相对平衡的配比。
整个一年级期间,虽然唐旭所住寝室在过道的对面,但彼此的距离很近,我们能常在两个时间里相互见上一面:一是中午吃饭的时间。那时的学校食堂不像今天的大学食堂,有宽阔的用餐大厅,因为没有用餐的大堂,同学们都是去食堂打饭回寝室里吃,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同学们会彼此串串门。二是晚自习以后的时间。八十年代初,由于四川省委党校与当时的四川财经学院之间,曾经就四川财经学院学校被占问题发生过争执,记得是一九八零年,学校还组成了学生请愿团到过北京,后经调停,学校校址之争算是平息了。但是,在四川省没有正式为四川财经学院划拨扩大校区的土地之前,两家学校在地界上一直存在着交叉,也正是因为这个,我们上课和晚自习的教室大多数在党校那边。按照学校规定,晚上十点过一点,教室管理员就会来关教室。大家回到寝室,稍稍休息一会,也就到了十一点寝室熄灯时间,同学们也总是在这时候才去楼层拐角处的洗潄间洗漱,如果有不愿睡或不能入睡的,便利用过道上的灯光聊天。
一九八零年的下半年,新的学生宿舍建好了,我们全都搬进了新学生宿舍。自我们搬进新的宿舍楼后,尽管还在一个楼里,但不一个班的同学相互之间见面的机会也就很少了,加上我和唐旭也不在一个大班里,除了像数学、党史等公共课在一起上,可能见上一面外,其它的见面机会也就相对少了。
我和唐旭是同一代人,都是在那个快要将我们淘汰的历史时刻,靠着自己的一份努力,从不幸运的一代人中脱颖出来的。而且后来还知道,在上大学之前,我和唐旭有些经历甚至是相近和相同的,但尽管这样,我和唐旭却不是同一类学生。
唐旭,总是那样沉静、听话、好学,对所有同学最有评价权力和说服力的就是当初负责管理学生生活的陈老师了,记得有一次几个同学打赌,然后我去剃了光头,一走进金融系办公室,陈老师就半嗔半笑的说:“要么,头发长得耳朵都找不着,要么,就弄成个和尚头,真不知道怎么那么调皮”。我相信,今天跟所有大学同学说,我在当时被慈祥如母亲一般的陈老师骂过,一百一十九个同学都不会觉得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但是,如果有人说:唐旭在大学的时候,被陈老师批评过,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一百一十九个同学,一定会指着说话人的鼻子说:“你一定搞错了,那是不可能的!”。
唐旭是对自己要做什么、要怎样做,有着比较成熟的想法和安排的那一类思想成熟的男人。可我不是,尽管我年龄上比唐旭只小一岁,并且在进入大学之前也有过与唐旭同样的生活经历,但我在四年大学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几乎可以用“桀骜不驯”这四个字来概括。我是属于那种“本质善良,但个性乖戾”,行为表现与内心世界存在着显著悖论的人。
今天认真分析起来,我和唐旭以及所有和我们同一个时代的人们,曾经被迫用还不成熟的灵魂,共同面对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共同承受了不属于我们那一代人的贫困和排斥,进而滋生了一种世界观上的内在失衡,而这个失衡最终又具体表现在:我们的大学生活乃至后来整个生活历程,隐约保持着一种心理状态,那就是:刚毅而坚强的外表下,总有着些许脆弱的成分。为了改变这种脆弱,抹平思想和情感上深深的创痕,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进取者,大致分别在以下两种人生状态中进行了抉择:一种是以加倍的努力,为某种荣誉而生存;另一种则是以玩世和抗逆,把自己个性上脆弱的成分掩盖起来。这里我想说的是:唐旭,是选择了前者的典型。
以现在的观点来观察,大学时期,大多数同学均抱着属于各自的想法,各自按照自己的个性不加修饰地在生活中表达自己,全年级一百二十个同学,真正有着成熟和长远设计,并在毕业那一年考研究生的人并不多,唐旭就是不多的同学中的一个。
三年级的第二学期的时候,有一次在党校那边的九教室自习,中间出来休息的时候,在那个干涸了的水池旁边,碰到了正好也出来休息的唐旭,于是我们在水池边聊了起来,唐旭的脸上总是挂着男同学少有的笑容,和蔼的表情总是会给人一种信任。聊的什么,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但记得起的是,只有那一次,是在大学里跟唐旭面对面地交流时间最长的一次。记得最后是他提醒说:“得回去收拾书包了,一会老婆婆要来关教室了”。当时管理学校这边教室的教工是老两口,于是我们都习惯按照四川方言叫那个女管理员“老婆婆”,其实人家也许并不老,大家这样称呼也可能是表达了一种复杂的心理,一方面,在四川,“老婆婆”本来是对年长妇女的一种尊称,而另一方面呢,也可能是表达着某种情绪,因为这个“老婆婆”来关教室门的时候,总是大嗓门,然而,对于教室里还沉浸在学习静默中的同学们来说,大嗓门的确是一种可怕的刺激。
一九八六年,也就是我回到父母所在的那个小县城后的第三年,自己也在反复思考后,决定放弃工作,甚至放弃原来想得很好的要承担起来的那些亲情责任,将刚刚组建起来并且在各方面都还很稚嫩的家,丢在那个偏远的县城,一个人独自回到成都。
就在上硕士研究生的第二年,由于曾康霖老师的努力争取,总行研究生部同意西南财大以金融系为主,派研究生到五道口听课。一九八八年新年刚过,季节还处在隆冬的时候,我和金融系研究生班的另外八个同学一块到了五道口。
这是大学毕业五年后,第一次见到唐旭,唐旭呢,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总行研究生部,我去听课的时候,唐旭已经任教务处处长了,唐旭的夫人也刚刚才从成都调到北京,一家人还住在研究生大院里一间狭小、简陋的宿舍里。
那次听课历时一个月时间,但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至今一直记忆犹新。
一九八八年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周日没有课的时候,便想出去看看北京的名胜古迹。那时家境贫困,为了节省乘车费,在一个周末,借了唐旭的自行车,骑着去了圆明园、颐和园。去的那天,北京风很大,于是出现了与在成都骑车完全不同的可笑现象:当逆着风骑的时候,即使下坡的路,也得使劲用脚踏,否则就根本走不动。
出乎我意料的是,在去玩了回来后的差不多一周时间里,脸就像有无数条小刀口被撒了盐似的不舒服,于是我问唐旭是怎么回事。
“你没有看北京的妇女们脸上都蒙着纱巾吗?”唐旭说。
“为什么?”
“风沙啊?”
“女的可以蒙纱巾,男人怎么办,比如说我,总不能也弄块纱巾来蒙在脸上吧?”
“北京男人们都是习惯了的。”
这次听课期间发生的另一件多少与唐旭有关的事,是刘鸿儒老师对我们来听课的同学逃课提出了批评的事。当年,我们一行到北京听课的同学共十一个人,金融系九个,农经系两个,加上陕西财经学院的四个同学,共有十五人。研究生部除让我们跟随研究生部本部课程安排听课外,还专门为我们这十五个同学开了几次课,但后来反映说,来听课的同学不认真听课,有的同学除了周末外出玩耍外,还在平时专为我们十五个同学开课时也逃课,甚至说,逃课的主要是西南财大(那时,四川财经学院更名为西南财大)的学生。
刘鸿儒老师当时还是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听了这个反映后,当然很是生气,觉得我们不珍惜听课机会。在我离开北京回成都的时候,唐旭多少有些无可奈何地告诉我:“这次听课反映很不好,据说曾康霖老师得知刘行长发脾气后,也很生气。”
“我可是一次课都没有逃过”。我赶紧这样告诉唐旭,毕竟在这些听课的同学中,只有我是唐旭的同学。
不管怎样,听了唐旭的话,我也觉得心里很不好受,我相信,唐旭在这件事情也一样多少有些感到抑郁,毕竟他也是从西南财经大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