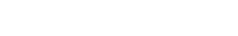此文已新浪原创上首发

三、师兄·师生
一九九一年,作为首批全国金融改革试点城市的重庆,为了要在金融改革方面有所作为,在市政府的支持下,重庆市人民银行在没有得到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情况下,批准了重庆西南第三制药厂发行可转换浮动利率债券。债券发行后不久,人民银行总行打了电话来严厉批评,于是,决定由我跟着重庆人民银行老行长一同到北京去做检讨。
这一次到北京,我去了唐旭的家,那时候,唐旭家已经分到了人民大学那边白石桥路东双榆树的房子,唐旭的四叔正好也在北京。一九九一年这一次发行浮动利率债券,以及我和老行长到北京检讨,实际成为后来一九九三年跟唐旭之间的同学关系进一步密切的外在原因。
债券发行尽管违反了人民银行总行的规定,但操作却是规范的。因为在发行之前,由我带头起草了《可转换浮动利率债券发行章程》,这个章程规定:除了利率实行浮动外,还将在适当的时候对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届时,债券持有人可自愿选择优先转换成为企业普通股票。到了一九九三年,全国股票市场已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一九九一年所有购买了“西南药业可转换浮动利率债券”的投资者,都急切地希望能够实现债券转股票,而这种希望,旋即也就成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及市人民银行的一种潜在压力。
国家证券监督委员会成立之初时,几个关键部门是由原人民银行总行金融行政管理司工作人员组成的,我呢,因工作需要曾经跟这些工作人员有过较多的交道。市政府和人民银行基于这一点考虑,加上所在职位决定,一九九三年五月,我以重庆市证券委成员和人民银行金融行政管理处负责人的身份,受委派到北京来联系重庆市企业推荐上市的相关工作。
到了北京后,向证监会熟人一打听,得知初审西南药业的工作人员是刚从五道口毕业的研究生,显然,我是不认识的,于是找到了唐旭,唐旭爽快地帮我约见了该人。
一九八八年,我从五道口听课回去后,与唐旭没有太多联系,所以,这也算是时隔五年之后,因为工作契机,我和唐旭的联系又开始紧密起来,而这一切,表面上是因为重庆市企业推荐上市工作需要,但真正的内在原因却是缘于从那时候起,我就蒙生了要到五道口考刘鸿儒老师的博士研究生的念头。一九九三年,为了重庆首批企业如西南药业、渝钛白、渝开发等上市,我频繁地到北京出差,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把要考刘鸿儒老师的博士研究生的想法告知唐旭。我同时还告诉了唐旭为什么想考研究生的原因。
今天想起来,如果要去深究潜藏在内心深层的心理原因,也许并不像我最初所表达出来的那样纯正。那时的我,还只有三十岁出头,强烈的俗世功利期望和对人生虚荣的追逐,迫使着自己的内心世界正进行着宏大和规模化的思考,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心理原因,但是,那时那刻,我只告诉了唐旭我内心世界的另一个也许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重庆是个码头文化气息比较典型的城市,这种社会生活生态,也许是受历史上像袍哥那样的民间组织体系内部伦理规则影响,人际社会或多或少把那样一些不能简单用好与不好来评说的东西传承了下来的。从本质上说,我也不能说我就绝对不适应那样的城市文化,因为在重庆的金融圈子里,因为自己的工作能力和行事风格,在年轻的一代人眼里,我似乎就是毕业后在金融领域工作的那一代学生中 “教父”一样的人物。当世俗荣誉和不羁个性与善良和正义本质之间形成某种显著冲突的时候,唯一能解脱自己的就是对一切过程进行反思。在不断地人生自我检视过程中,真正让我深深疼痛的是一些被自己悟到的人生悖论:在文化知识、智力、才能与个性之间,在行为方式与理性追求之间,在亲情与个人情感之间,在善良的本质与多少有些恶作剧的爱好之间,在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遵从与对自由界限的痛恨之间,等等,等等,无一不在以血淋淋的结论证明我内心世界的冲突。
以哲学的观点看,在我们国家,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无论是平民化的生活领域,还是等级明确的主流社会领域,总是“明规则”与“潜规则”在共同发生着作用,甚至在一些特殊的社会生活领域,潜规则的作用较明规则更为有效,至于这个潜规则是由“码头文化”,还是由我们儒家“唯上唯尊”的文化来规定,这本身并不表明作为个体的人,可以在“明规则”和“潜规则”中进行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回顾,我告诉唐旭的可能只是其中一个非重要原因,但尽管这样,我自视我并没有刻意在唐旭面前保留什么。
“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听说你在重庆金融界还小有名气。”
“那只是表面现象,当然,以今天我的事业状态,要交点事给我办,只要不是‘揽月捉鳖’那样的难事,我还是有能力去做的,但显然,这不应该是我的志向所在”。
“你可以报名,但必须考过北京市规定的分数线,至于要上刘鸿儒老师的研究生,我只能努力帮你跟刘老师联系。”
唐旭如此说,显然是有意识地回避关于要离开重庆的原因讨论。其实,这时候,我也许是不了解唐旭的,总觉得他这样回答一个老同学,多少有些冷冰冰不近情理。因为在当时考博士研究生,尤其是考刘老师的博士研究生,除了基本成绩外,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在单位工作经验和具有一定科研成果。而以我当时的情况,不仅在重庆金融界小有名气,而且在《金融研究》和其它一些杂志上也发表过文章,应该大体上是符合刘鸿儒老师对应考生的条件偏好的。关于唐旭为什么要那样冷冰冰地对待我这样一个老同学,在后来与唐旭的交往不断加深过程中才渐渐体会到的其中的原因:那是唐旭做人风格的一个侧面――可以努力提供帮助,但不轻易作任何承诺。
为了背水一战,置自己于死地而后生,一九九四年初,也就是报名后不久,在得到人民银行重庆分行时任行长关于暂时不用退还单位住房的承诺后,我辞去了重庆人民银行金融行政管理处负责人职务,只身去了已经步入萧条的海口。在那里,一边准备考试复习,一边开始反省自己在重庆市近五年的工作和生活。
一九九四年五月,我在焦虑中接到了五道口的《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拿着录取通知书,带着疲惫的身心回到重庆家里,休息了整整三个月后,才怀着一种脱胎换骨的心情,启程前往北京。
从首都机场到五道口的出租车,大约要走五十分钟。一路上,除了贪婪地领略机场路两边高耸的杨树和北方才有的独特阳光外,多少感受到了内心难以抑制的激动。在那时那刻,想得最多的并不是如愿以偿的到五道口上了刘鸿儒老师的博士研究生,而是觉得自己可以洗去身上的尘土,再次获得人生重新选择的机会。众所周知,在当时的社会生存环境下,因为住房、因为人事档案等外在限制,一个人想要以一种体面而且低成本的方式获得重新选择的机会,那是非常困难的。
我深知此次负笈北上,机会之获得,自然是有唐旭的关照和帮助成分的,但没有想到的是,唐旭的这种关照和帮助,在以后我在五道口的三年上学过程中,升华成为他对我这个老同学的宽厚和眷顾。
第一件事是发生在一九九六年的一次车祸。
记得那是一九九六年的夏天,外地来了金融七九的同学,相约一起去吃饭,我和唐旭都去了,席间,不知不觉喝多了。去的时候,我和唐旭共同开的是我朋友刚买的一辆新的本田雅阁,吃完饭回家的时候,先是唐旭开,到了他家楼下,他看我有些醉了,于是坚持要送我回学校宿舍。当时他家住海淀塔院,从塔院往西一个路口再向北,从北四环路口再往西,到我住的展春院博士宿舍,也就两公里路程。
可是我坚决不要他送,趁着酒劲把他从驾驶室里拽了下来,可是唐旭呢,仍然秉承了他的宽厚秉性,也不坚持,下车后只是不停地说:“老侯,你行还是不行?”。在我坐上驾驶室后,几乎就没有听唐旭说什么,关上车门,一踩油门一溜烟就把车开走了。可是,开出去还不到一百米,酒劲就上来了。当车到知春路口时,醉意之中没有过红绿灯,车就向南转去,逆着元代古城墙东边的单行线,把车开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沿途一共撞了两辆130货车,朋友新车的两边气囊也都给撞爆了出来。
那时候的北京,对酒后驾车控制还不像今天那样严,但交警还是将我送到北医三院作了血液化验,按照当时的交规规定,测出来的酒精浓度完全达到了可拘留的水平。好在,那晚执勤的交警见我人还清醒,同时也看了我的学生证,交警也就没有再坚持要拘留我。
无独有偶的是,手机没有电了,处理完交通事故回家已是深夜一点。第二天早晨去学校,在学校大门见着了唐旭。
“老侯,昨晚怎么啦,打电话说关机,是不是出事了?”唐旭一见我就问。
我只好如实将头天晚上那惊险的一幕告诉了他。
“我真后悔没有坚持把你送回宿舍!”
“你做不到的,我们俩换个位置,我是你,你是我,昨晚就没事了,呵呵。”我调侃地说道。
其实,我虽然是以玩笑方式说,但从内心讲,那就是事实。以唐旭的谦和,他是绝不愿意主观上去勉强任何人的,更何况是我这样一个有时候几乎有点不那么讲道理的老同学。
第二件事是关于我的学位论文写作和定稿的事。
一九九六年上半年,五道口的学习进入了二年级第二学期,课程学分早已休满了,接着就到了该撰写学位论文的时候了。三月份从重庆回到学校后,我试着初拟了一个写作提纲,交给了刘老师。那时候,刘老师还在证监会主席任上,工作也很忙,刘老师拿到提纲后,没有时间细看,要我先将写作大纲交给副导师虞关涛老师看一下,于是我将写作大纲送到京广大厦北面的呼家楼附近的虞关涛老师家,按照习惯,虞关涛老师自然是要先问:刘老师对这个论文写作大纲是什么意见?我如实说:是刘老师让我交给他看的,于是虞老师说他没有意见。
我以电话方式将虞关涛老师的话如实转呈给了刘老师,刘老师说:“那你就这样先写吧”。当我花了将近三个月时间,将论文写成一个约八万字左右的初稿,交给刘老师的时候,刘老师的话,让我整个人凉了半截。
“侯合心,书读得太少了吧。”刘老师粗略地看了看我的稿件后,很严肃地对我说。
我无法对刘老师的带有批评语气的话做出任何反应,我相信刘老师的话是指我经济学方面的书看得太少了,但无论如何,刘老师的这句话,对我这个学生、一个正在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成年人来说,应该算是极重的了。
回到宿舍后,我反复自问:我什么时候系统地读过几本经济学原著了?即使读了一些,也不过是应付专业课考试而已。这样一想,似乎觉得刘老师说的就是事实,并没有什么不对的。
※ ※ ※
回想起来,在大学的时候,自己的确没有认真看什么经济学书籍,反倒是利用学校的图书馆藏书,把个欧洲文学,什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看了个遍。看完了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大家的,又看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左拉、司汤达等人的。受当时的政治气候局限,那时的大学图书馆也不是什么书都有,比如布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爱尔兰作家詹姆士·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等,我就没有找着,为了实现所谓“饱览群书”的目的,像上面这些书,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也都一一找来补看了。
后来上硕士研究生,也没有认真地读太多的经济学书籍,而是大量阅读历史、宗教、音乐欣赏、文艺批评等书籍。看得最多的是欧洲历史书,什么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蒙森、詹姆士·吉本等著名历史学家的书都找来看一个遍。在今天看来,读了这些书,对我自己的文化修养是不是就一定有益,当时是无法做出评价的,但是,到后来自己转而研究政治哲学的时候,当年读的这些历史书,才显示了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历史学知识,尤其是"Democracy"(民主政治)发祥地的欧洲历史学知识,是一个人提高自身政治哲学素养不可或缺的基础。
即使是上博士研究生期间,虽然也看了一些经济学原著,但与一个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的专业著作阅读量要求相比,可能仍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一期间,我开始大量研究政治学著作,如孟德斯鸠、约翰·洛克、卢梭、托克维尔、大卫·休谟、拿破仑、马基雅维利、汉弥尔顿等人的著作,到后来,甚至连现代以研究社会正义而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的著作也都找来研究。
刘老师这句话,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多少还是有些觉得自尊心受伤的,但的确也是受到刘老师这一次严厉批评的鞭策,毕业后,我发疯似地阅读古典经济学著作,从托马斯·孟的开始,沿着古典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轨迹,把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巴斯蒂特·萨伊等人的著作全看了个遍。凯恩斯不算是古典经济学家吧,也不管了,把他的著作也拿来读了个遍,甚至连写凯恩斯的几本著名传记学著作,也都通看了一遍。
最让我觉得自己有点疯的是,由于阅读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二卷,必须要看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原著,否则很难弄清楚那场著名经济学争论的主要内容和过程。而这本书只在一九六二年时作为批判性研究资料在国内出版过一次,以后,自然也就不会再出版了,因为我们是坚决反对马尔萨斯的(当然,后果就是今天乃至今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的社会发展都将背负着沉重的人口负担)。
为了找到这本书,我上“孔夫子旧书网”去淘,还真的找到了,但是价格高达一百五十元!而且只有六成新。书寄来后,翻开底页一看,标价竟然只有一块六毛钱!好在我是学经济学的,知道通货膨胀是历史价格倒算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将近一百倍的通胀率!卖书的商家尽管奇货可居,但多少还是太狠了点。
看完这些书,深深体会到刘老师基于师道严厉,批评得一点都没有错。至于为什么要从古典经济学原著看起,我相信,即使是后来集经济学大成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没有超出于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基本经济学概念和逻辑范围。就是开创货币经济学的凯恩斯,即使是革了古典经济学的“命”,但在我看来,其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冲突,也并不是在微观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伦理上,而是在经济学的政治伦理原则问题上。
其实现在想来,刘鸿儒老师对他的学生说重话,这符合他这样一个学者大家的个性(虽然他当时还是政府官员)。因为更能体现刘老师治学严厉的事还有一件,那后果比给一个学生严厉批评要严重得多。
我们九四级博士研究生一共有七个同学,除了我和少数几个同学守在学校读完三年外,大多同学都是在学分修满后,就纷纷先去了工作单位,边工作边写论文。一九九七年,就在我论文答辩通过后不久,我们中的一个同学回研究生部答辩。这位同学论文答辩的那天我参加了,在答辩委员会上,他的论文是同意通过了的,但是,后来的事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刘老师当时是研究生部的学位委员会主席,论文答辩结束后,必须由学位委员会主席审查相关答辩记录,认同答辩记录之后,金融研究所所长才可以和刘老师共同在学生的学位证书上签字。那位同学的答辩记录是刘鸿儒老师出差回来后补阅的,当刘老师看了那位同学的答辩记录,并找来当时做答辩记录的工作人员询问了答辩的相关情况后,刘老师甚至都不照顾那位同学导师的面子,就把那位同学的学位论文给否了。
在那个文凭快要被铜臭淹没的年代里,刘老师应该算是还在坚持着要维护文化质量和尊严的不多的几个大家之一了。后来,我从唐旭在对待一些官员要来五道口上研究生的态度上也体会到,刘老师的这种宁缺勿滥的治学品格,完全被唐旭继承了下来。
关于唐旭继承刘鸿儒老师治学品格这一点,也有一件事较为典型。记得还是我在校期间,南方一家银行的地市级分行副行长,是从政府官员转来银行工作的,到五道口跟着研究生听过很多次课,因为年纪都比较大,所以,我们彼此之间都混得比较熟了,也许他也知道我和唐旭之间的关系,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可否以在五道口听课为由,能够让唐主任给发个什么文凭。我知道,对于从政府转到银行来的人,如果有一个金融方面的文凭,对今后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更何况是总行研究生部的文凭,碍于面子,我答应帮着问问。
当然,我也忠实我对别人的承诺,找到了唐旭,可唐旭很简单地就回绝了。
“老侯,我这里只有国家正式文凭,要么硕士,要么博士,没有其它文凭可发,那两个文凭,可是必须要按程序来的,这个你知道。”
唐旭如是说,自然我也就没有理由再说什么,排除那位相托之人与我之间的个人良好关系不说,仅仅单就文凭一事来说,我其实也是个对那些简历中没有国民脱产教育经历,但却是“既赚了官位,又捞了文凭”的投机类群非常反感的人。
※ ※ ※
刘老师严厉地说了我的那天晚上,其实还是很难过的,但不管心里怎样不舒服,既然老师说了,事情的严重性自然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不能不认真对待。整整一个晚上,脑子乱得一锅粥似的,甚至都不知该怎么办了,那么短的时间就要毕业答辩,重新大量阅读经济学著作,时间上几乎是不允许的,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换题目,可怎么换?脑子一遍空白,临睡前,终于想到了一招:去找唐旭。
唐旭也是刘鸿儒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只是比我高两届,所以,也算是师兄,他头一年刚刚通过论文答辩,他的学位论文题目是《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答辩通过后,唐旭还把他的学位论文给了我一本。
第二天一早我去唐旭办公室,对他说了关于我的论文遭遇困境的事。
“唐旭,我现在脑子就是一锅粥,换什么题目,我昨晚想了一晚上都没有想出来”。
“老侯,先想想这些年你都干了什么工作吧”唐旭说。
“银行、证券、金融监管啊?”我说。
“那不就对了吗,写与你干过的工作相关联的题目,这样写起来会有实感一些,也容易见成效。”
经唐旭一点拨,自己似乎豁然透亮了,真有点大梦初醒的味道。禁不住在心里想:自己过去明明就心不在经济学,反而去写理论性很强的题目,写不好,被刘老师重责,活该。
“我给你个题目:‘我国资金问题与融资结构研究’,具体题目怎么定,你再想一下,但围绕这个中心来写”。唐旭接着又说。
对我来说,唐旭代为拟定的题目的确具有很强针对性。融资结构本身就是讨论既定经济体制下,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金融效率,一个银行、一个市场,正好是过去自己工作的领域。
后来,根据唐旭的提示,把学位论文题目定为《直接融资发展与我国经济现实问题研究》,大约利用两个月时间,夜以继日地看了托宾、莫利迪安尼、马柯·维兹、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一些经济、金融学家的理论著作,终于将论文写成。
一九九七年,论文正式答辩前的一个月,我再一次将论文交到刘老师手里,几天后,刘老师来学校讲课,让我去他的课间休息室。这次见到刘老师,表情已不再像第一次那么严肃得吓人。
“给虞关涛老师看一下,让他给你看看英文摘要,虞老师可是英语专家哟,如果他看了论文后认为没有问题,就这样定稿。”
听到刘老师如此轻松的语气,一颗一直悬着的心,才算落到了底。
第三件事也许就是唐旭对我这个老同学的纯粹眷顾了。
一九九六年冬天,加拿大蒙特利尔McGill University给了研究生部一个四十五天时间的全资助学习考察名额,唐旭把这个名额给了我。
至今还记得那天到唐旭办公室的情景。
“老侯,给你一次练习英语的机会”。我一进门唐旭就对我说。
以我这样的靠着在大学从ABC开始学起的英文学习经历,阅读、笔写还勉强可以,听力和口语是无论如何都难以药救了。我一看他给我的日程表,除了一次到多伦多Royal Bank作银行业务拜访,和一次到渥太华加拿大中央银行参观外,大多在蒙特利尔的McGill University做功课。
足以证明四十五天时间,对练好口语、听力实在是太短了的一件事,发生在我在McGill University访学期间的一次消防演习。
那天,学校突然响起了警报,隔壁的一位女老师来敲我的门。
“Sir ,There are fire drills ,go out door.”
“Don’t forget bring your jacket”。 当我都已经走出门了的时候,那个女老师又补了一句。
于是,我又匆匆忙忙地回到那间小办公室,把桌上的书和资料全部收到公文包里带了出去。到了教学大楼外面,场地里站满了老师和学生。让我极不自然的是,刚才那位女老师用怪怪地眼神看着我。
那时正值十一月份,蒙特利尔因为纬度较高而早已进入浓冬,学校大楼早已供暖。因为暖气较大,每天早晨我一进办公室,总是习惯性地把外套脱下来挂着衣架上。
站在大楼外的全部师生都穿着外套,只有我一个人还只穿着衬衣,直到冷气透过衬衣,一阵一阵袭向敏感的肌肤的时候,我才想起,那个女老师说的不是:“Don’t forget bring your book”,而是说不要忘了带上外套,英语发音里,jacket后面的“et”,几乎是不发音的。想起那个女老师用怪怪的眼神看着我,我不禁觉得自己多少有些滑稽。
英语口语、听力是没有多大提高的,不过,在McGill University期间,正好利用了他们丰富和开放的图书资料,查阅了加拿大和OECD国家的企业融资结构资料。回国后在论文答辩前,对论文的实证部分相应补充了国际比较内容,论文也就显得更加丰富了。
也是过了很久,才回味唐旭所谓:“给你个练英语机会”这一说的良苦用心。他不会不知道学习一门语言的规律,对于我这个年纪已越过语言学习适应期的人来说,四十五天时间显然太短,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真的对口语和听力有显著改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是想淡化他对我这个同学的特殊眷顾之情,想以一种“拒绝感恩”的方式告诉我这件事。
一九九七年的四月,我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接着就是找工作了。先报了人民银行总行,准备考公务员,然后到金融研究所去。有一天我跟唐旭说到这事,唐旭表达了他的想法,他觉得我去人民银行的话,可能在调家属问题上会慢一些。
“要不,直接去专业银行?那样会快一些把家属调过来。”
“可以啊?去哪家行好啊”。我说。
“去建总行吧,人力资源部那里我比较熟悉,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去报名考试就是了,以你的资历,考试通过应该不成问题”。
“其实,最好是有一个单位能一举把夫人调动和房子问题全解决了。” 唐旭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后来中国投资银行来学校挑选学生,唐旭竭力推荐了我,并向对方说,因为我年纪较大,而且是有职务来上的学,可能在家属调动和住房问题上需要解决的迫切性会高一些。谁知当时的中国投资银行行长对唐旭提到的问题,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
在去中国投资银行正式报到之前的这段时间,由于新生要入学,我得搬出博士研究生宿舍,投资银行临时安排我住在离上班很远的一个宿舍楼的地下室集体宿舍。唐旭知道,像我这样在重庆优越惯了的人,加上年纪一大把,会住不惯。
“住我那里吧,我楼下正好有一个一室一厅,是单位补面积时给的,没有人住”。唐旭对我说。
“好吧,你不会管住还管我吃吧?我可是个怕被管的人哟。”我还是用调侃的说话习惯回答唐旭的关心。
“呵呵,谁敢管你老侯。” 以后,唐旭如我们双方之约,从来不来管我,也不叫我,一直到我搬走。这可能是因为唐旭太了解我了,知道我是个散漫自由惯了的人,不善被任何东西所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