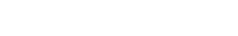此文已新浪原创上首发
今天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写给唐旭的这篇一半是讲述、一半是祭典的文章算是完稿了,可是,在手指离开电脑键盘的瞬间,我甚至不能把握它是不是足以支撑起我和唐旭之间这份深厚的同学情谊,也不知是否足以向着枕息于天堂之上的亡灵,完整、真实地诉说属于我的一份凝重和哀思。无奈之下,我再次一个人开车去了八宝山……
站在唐旭的墓前,看着碑刻上那永远不会再改变的音容,一切似乎还是那么熟悉,眼前的一切,就如我心中所冥想的一切那样真实,于是我问自己:我和生时的唐旭之间,早就已经无所禁忌地敞开我们灵魂的真实,都想着要无欺坦然地对待彼此,对待这个世界,对待身边所有的人,难道在唐旭乘鹤西去后,我还有理由来改变这一切吗……
一、写在前面的哀思
今天,是公元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算了一下,如果从今天我动笔写这篇祭典文章为截止点,唐旭离世而去的时间已经整整一百一十五天。
此刻,是公元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时十分,也就是一百一十五天前的这个时候,唐旭俯视尘世,飘然仙去……
在没有动笔的这段日子里,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才能写好这篇反映我和唐旭之间真实与真诚友谊,以及对唐旭英年早逝深切哀悼的纪念文章。经过细细思索后,断定自己可能没有智慧和笔力来独立地描述一个完整的唐旭,如果真的能够表达一缕对老同学的哀切之情的话,所能写的也只能是我和唐旭之间的交往以及在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且如今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点点滴滴真实记忆。
我和唐旭,是从同学到师兄,然后从师兄到朋友,最后,再从一切复杂的外在关系结构中,回归和升华到朴素同学关系上来的。我们之间因为学习、工作以及朋友往来中所构成的一切,与这个世界上所有普通的友情一样,其外在表现并没有什么太多区别,但是,我们两人都没有说出来的“同学友谊”四个字所装载的友谊内容,却是一般情谊无法简单涵盖的。
动笔之前和动笔之后,我的内心始终很纠结,自唐旭不幸离开人世之后,每每想到必须写好这样一篇属于我和他而不属于任何俗世虚荣的文章,就会在瞬间滋生出一种莫可名状的心乱如麻。为了解决这样一种情感和心理过程,我不断地检索我们之间那些俗务相托、同学眷顾的种种情景,而这些,无一处不关乎到我和唐旭对社会、亲情和男人责任的不同或相同理解,难以规避的是,文章既要写唐旭,也不得不写我自己,不这样,似乎就无法把一个真实而有血有肉的唐旭写出来。正是因为这个,我只能对我和唐旭共同拥有的全体同学们说:如果这篇文章有幸能在新浪网的读书专栏上登载,当你们看到它的时候,除了友善地痛责我之文笔拙劣外,也同时要能够理解我的这份苦衷。
在此之前,唐旭夫人和唐旭生前的一些朋友均一再向我提到,相关报纸或刊物登载了关于唐旭的纪念性文章,并且说写得很感人,但我一直回避去看这些文章。因为,我之心乱如麻,除了会在某一个思绪过程的瞬间,不相信“唐旭已去”这样一个残酷现实外,还会担心自己的笔触不当,会在无意中损害了一个我们大家都真诚敬仰和爱戴的唐旭。四月份我还在昆明的时候,我将我的这种担心向丽莎同学说起,丽莎同学及时回了我的信,回信尽管很简短,但我相信她说的可能就是金融七九所有真正懂得唐旭,同时也懂得从生活审美去看待一个生命之来与去的同学们所期待的。
酝酿动笔之前,四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我从昆明回京的第四天,我和我夫人开车去八宝山公墓看望了唐旭,在一排排已故者中,唐旭在至下而上的第二排的中间,我依稀记得位置号是2285,这个位置是二月十日我送唐旭夫人去八宝山时她定下的。花束遮住了墓位号,我本可以轻轻移开花束,证明自己那依稀的记忆,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去拨弄那一缕花束,我想:唐旭应该享有属于他的宁静。
看过唐旭墓碑上的祭典文字,配着烧制在磁砖上的是一张学者气很浓的照片,任何站立在这块祭典唐旭土地上的人,当他面对如此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如果还能回忆起唐旭的学业和事业辉煌历程,都会从这张照片和烧制在墓碑上的文字体会到:那就是唐旭一生事业过程的再现。
当我默默站在唐旭墓前的时候,不经意中便会想:枕息在那块并不宽大的墓碑后面的唐旭,他如今怎样了?甚至也联想到三月十日,我和唐旭的夫人、侄儿去殡仪馆迎接唐旭骨灰时的情景:在三个人之中,我是唯一与唐旭没有亲情关联的人,但是,我和唐旭的两个亲人一样,共同完成迎接唐旭骨灰的全部仪式……
殡仪馆的两位衣着制服的司礼,按照规定的程序从存放处的里间把骨灰盒捧出来,并解开了盛殓唐旭骨灰的红色专用布袋。
“那就是唐旭!”当看到唐旭洁白的骨灰那一瞬间当,我的思想和我的情感不自觉地这样惊呼!几个月前,唐旭,还是我可以与之交谈的鲜活生命,几个月后的今天,完整的身体、情感和智慧,都只能寄托给不再可知的后人世界。
“再也没有那么好的朋友了吧?”
我夫人的一句话,将我从痛苦的冥想中拉了回来。
“不,应该说,像唐旭那样的好朋友不会再有了”。
我夫人可能是没有办法理解其中之意的,因为,她所看到的,仅仅是我和唐旭、还有我们两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唐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谦和有加、温文尔雅的对事待人态度。
“花也不买一束”。夫人又嘀咕了一句。的确,看唐旭的墓和墓墙周边的逝者,几乎每一个墓碑前都放置着花束。
听了夫人的话,我心里想:这就是我和唐旭。
记得一九九八年,我的家刚从重庆搬来北京的时候,第一年在北京过春节,对要不要按照中国传统习惯相互给对方的孩子发压岁钱的问题,我和唐旭曾经进行过一次简单的讨论。最后是唐旭说,我们两家之间应该舍弃繁文缛节。以后,我们两人都遵守了这个约定。
越是追忆自一九九一年以来,我与唐旭逐渐走近的那些点点滴滴,就越是觉得有更多在当时看来可能很简单的事情,需要或者值得我去思索和回味,而越是思索和回味,也就越是希望等到自己对所有事情理解得更全面或更深刻一些的时候才来动笔。但是,当五月三日夜,我在梦中见到了唐旭以后,一种情感上的催促力量让我的内心无法再耽于自己的规避心理,我不能再担心自己文字描述能力的局限,而将这篇文章再这样延宕下去。
于是,不再纠结于不必要或者说无法完美的细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