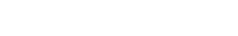获知唐旭生病的消息,我的心揪紧了。我把电话打到他家里,电话那端的唐旭说:“没什么,病已经生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想办法治疗就是了”。他的语调之平静,出乎我的意料,反倒让我把许多准备好的安慰话收了起来。我多次去看他,在他北京的家里。他在上海住院手术期间,我也去了两次。每次,我们不谈病情,更多的是谈五道口,谈学校的那些人和事,谈学校的过去和将来。他始终乐呵呵的,在他的脸上,看不到病人的痛苦、惶恐和苦闷。
唐旭乐观。
尽管病了,唐旭依然坚守工作岗位,边治疗,边工作着。他不仅在履行着反洗钱局局长的职责,而且这期间,五道口有活动,只要请到他,他都会来。学位委员会的会议、89级同学入校二十年后的母校聚会、博士生的答辩会,他都欣然前来。看着他因治疗用药而变暗且长满了痘的脸,我们都心里难受,但掩饰着不流露,就为了让他继续快乐着。唐旭就这样坚持工作着,直到病魔让他倒下无法站起,无法行走。
唐旭坚强。
1月31日,2011年1月的最后一天,也是唐旭生命的最后一日。这天下午,我们去看他,处于弥留之际的唐旭,似乎知道我们来了,手臂也似乎要尽量举起和我们打招呼,昭示着他的内心对生的向往,对五道口的留恋。
2个小时后,传来了他去世的讯息。
1985年,我刚到研究生部工作时,唐旭还是学生。翌年,唐旭毕业留校,我们成了同事,直至2007年初,他调到总行反洗钱局任局长,我们一起共事了21年。
那时的唐旭,三十出头,有些清瘦,一口绵绵的四川话不愠不火,语速不徐不疾,让人一听就知是付好脾气。穿着一件普通的夹克,总是很整洁。唐旭穿衣服只求干净、得体,不求牌子,几乎没见过他对品牌的评论和追求。在一个食堂吃饭,也从不挑剔。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喜好。他最难忘的,是在老家四川时,挑沙子、在长江边上当纤夫的苦难磨砺。
唐旭朴实。
那时的唐旭,家远在四川,尚未调进北京。住在独身宿舍的唐旭,工作之余的时光,都交给了读书,写作。很少在运动场见到他,更别说商场或其他娱乐场所。在那孤独的岁月里,书不仅充实他的理论基础,扩展了他的视野,让他有了更多更深入的思考,也慰藉了他的思乡之苦。夜幕下,办公室的灯光熄了,宿舍的灯光接着亮起。灯光下,只见唐旭埋首的身影。
唐旭刻苦。
在教务处工作,唐旭想的是教学内容怎样丰富,教学方式怎样灵活,学习生活如何管理。在科研处工作,唐旭想的是和金融实际,和总行的工作怎样紧密联系,来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又为总行工作服务。担负校领导后,他更操心学校的规范管理运作,学校的发展和未来,学生的培养和成长。正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研究生部的小平房拆掉了,建起了高楼,学生从原来8个人挤一间房的窘状下,搬入了2人一间有卫生间、有热水洗浴的寝室,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谁都知道,这么大的基建工程,作为一把手的唐旭,要操多少心啊。
唐旭认真。
在研究生部工作,接触最多的当然是学生。唐旭对学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从不摆架子,也不会摆架子,学生也乐意和他交流。对于招生,唐旭认为最重要的是公平。他说:“若没有研究生部招生的公平,我的今天不知会是什么样。”是的,不能让考生失去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会影响他们的一生。对于在校生,唐旭乐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改进学校的管理。对于学生的困难,也千方百计想法解决。每个年三十的年夜饭,唐旭都到学校和假期未能回家的学生一起聚餐,让学生过年不孤独。对于校友,他也时时惦记着。
唐旭人性。
2月12日,雪后的北京,空气有些清冽,早春的气温还很低。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外,站满了黑鸦鸦的数不清的人群。人们胸戴白花,手持黄白菊花,等待着送唐旭一程。校友们来了,从海内外,从全国各地,不分届别,不论远近。
人民银行的所有行领导都来了,银监会、证监会的领导也来了,那些唐旭生前工作过的单位的同事,工作联系很多的高法、高检、公安部、海关的人也来了,总行各司局各单位的同志也来了。
上午10时,哀乐响起,告别仪式开始的时候,天空中的云层多了、浓了,老天也悲戚着。
唐旭安卧在鲜花丛中,脸色平静安详,没有任何病患的痛苦。遗像上的唐旭灿灿笑着,看着自己的亲人、同事、朋友、校友。
愿唐旭在天堂也一直笑着。
李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