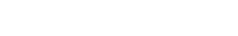推荐寄语:82级王令芬师姐推荐一篇有关儿童早期教育的文章;作者汪丁丁是一位经济学家。本文推荐给所有现在有幼小子女的校友们,希望对理解如何教育幼年子女有些帮助。
直觉的西方理解是笛卡尔在《探究真理的指导原则》里定义过的:在例如学习数学的过程中,若我们的心智关注着某一命题的论证,于是我们会从它的前提到它的结论,反复多次地审查,最后因熟悉而达到一种境界,就是能够直接从前提看到结论。笛卡尔说,这就是“直觉”(源自拉丁文的英文单词“intuition”)。这当然是典型的西方理解。在东方思想传统里,直觉首先含有诸如“悟”、“顿悟”、“开悟”、“渐悟”和“觉悟”这样的意思。若不考虑佛家对中国思想的影响,那么我们从老子、庄子、墨子的文字里仍可读到许多关于直觉的极不同于西方理解的中国理解。我的感受是,中国的直觉或东方的直觉,它的核心要素在于“表达”——文字和言语的表达不是直觉,甚至用文字和语言定义的“直觉”也不是直觉。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里,婴儿被认为是有直觉的。这两方面的感受,合起来考虑,我以为读者可以自己感受到我欲表达却不能表达的东方直觉。
今天,以我的阅读而言,人类胚胎发育的脑科学研究支持直觉教育(即尽量摆脱文言表达的教育)。例如,下述的教育顺序已在西方知识界有了相当程度的共识:(1)胎教的内容以听古典音乐和与母亲对话为主;(2)新生儿教育的内容以身体和眼睛的动作相互协调为主;(3)男孩在三岁以前,女孩在两岁(或18个月)以前,这一阶段的教育形式是模仿母亲和其他成年人的行为的同时学习母语;(4)三岁至五岁的儿童教育,主要内容是在儿童可感的母亲的关注范围之内与其他儿童的交往(主要是游戏)、观察与模仿、色彩与绘画、真实物体与几何图形的关系、行为的教养(公平感和文化传统)、符号文字的识别和使用;(5)五岁至七岁的儿童教育,如中国古人所言:洒扫、应对、进退。
上列的顺序,我们的家长(尤其是因无知而无畏的那些家长)不可随意颠倒,也不可随意增加诸如外语和数学这样的内容。事实上,人类儿童的脑结构发育,要在9岁以后才适合学习带有抽象规则的数学,要在12岁以后才适合学习母语之外的语言。以后者为例,双语儿童的问题研究表明,那些在母语学习期(0岁至3岁)被暴露在外语环境中的人类儿童,成年之后更容易发生情感表达的障碍。因为,人类只能用母语来表达最内在的情感,当上述儿童被暴露于母语和外语并存的环境内时,由于人类先天具备的语言学习能力,母语和外语被同时吸收,但人类的情感脑(即大脑右半球)完全不会同时用两种语言来表达情感。故而,习得母语之前的双语“教育”根本不被认为是教育,惟其如此,文献作者们使用的是“被暴露于”这样的描述。双语儿童(bilingual child)的情感表达问题,是儿童研究领域的历史悠久的主题,脑科学研究只不过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持。至于过早实行数学教育导致的儿童问题,迟至197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家西蒙(Herbert Simon)已关注并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在1980年代多次访问中国并与中科院心理学研究所建立了合作编写中学数学教材的科研项目。西蒙教授告诉过我,这套数学教材之所以特别有效,是因为中国以往的数学教材过早地抽象化了。我相信他的判断,因为我知道中国的数学教育深受1970年代以前苏联教育的影响。
又例如,上列第(4)阶段的教育内容,三岁至五岁,这时的儿童,已习得了母语,故可参与社会交往。前提是,必须在母亲的视线范围之内,更严格地说,是必须在儿童感觉中的母亲关注范围之内。因为,若我们在儿童的这一阶段感觉不到母亲的关注(我知道中国的许多儿童始终没有这一感觉),在我们的“哺乳动物脑”(limbic system,直译“外缘系统”)激发出紧张的情绪,临床分类就是“焦虑感”。由于我们在哺乳动物演化阶段已经形成的本能,一旦有了足够多的焦虑感,我们便无心他顾,陷入于“不安全”的紧张之内,不能自拔。许多临床观察表明,儿童可因此而憎恨“抛弃了他们”的母亲,表现为对母亲的冷漠和烦躁。我不愿意评论中国的母亲,在这样许多年的伟大转型期里,她们已经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可是,另一方面,她们当中有接近50%的比例将亲生子女交给子女的祖辈去照料,这就完全违背了例如日本家庭特别重视的“亲子接触”原理。作为经济学家,我明白导致了这一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经济政策自从1950年代以来,就始终强调“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从而极大地忽略了女性在亲生子女教养过程中无法估价的重要性。日本的家庭,至少在这一方面远为优越,因为日本的传统是:女性婚后不再出去工作。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居于世界首位,这是中国革命的遗产。
根据我的观察,周围的许多年轻家长不懂得梁漱溟早就阐述过的基于生命哲学的教育方法。我们的未来正走向毁灭,因为过分商业化的儿童早期教育和家长们自己教育的失败。这样,我计划写一系列早期教育的文章,从脑科学角度重申旧教育的正确方面和审理目前教育的可能不正确的方面。
脑科学视角下的儿童早期教育(之一)
汪丁丁
今天,家长们普遍关注儿童的早期教育。遗憾的是,主要由于中国教育事业的过分商业化,其次由于幼儿教育者的收入相对而言较低从而缺乏符合现代教育资格的幼教师资,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中国,儿童早期教育的方法与内容,普遍地不正确。所谓“正确”的知识,根据现代认识论的定义,就是在我们共同关注的知识领域内已经达成足够普遍共识的那些知识。与儿童早期教育密切相关的脑科学当代研究成果,在上世纪末叶已开始融入经济发达各国的教育过程。这篇文章,旨在概述脑科学视角下儿童早期教育的正确过程。
香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相关的合作单位自2002年以来发表的几篇脑呈像研究报告表明,以中文为母语的受试者目视英文时所激活的脑区,与以英文为母语的受试者目视英文时所激活的脑区有显著差异。这一差异的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对英文的辨识过程,伴随了比以英文为母语的人相比而言强烈得多的大脑右半球活动。换句话说,像形文字,既便已经被符号化到了今天这样的抽象程度,仍然激活了它的使用者的形象思维能力和社会认知能力。而拼音文字则只激活它的使用者的抽象思维能力(大脑左半球的若干脑区)。
以拼音文字为思考的基本方式的西方学者,处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里面从而被当时当地的社会交往过程不断地塑型着,怎样认识“心-身”关系呢?根据我的阅读,近代以来,在“央格鲁-美利坚”思想传统中,詹姆士、米德、和布鲁默尔的反思性观点影响最大。在欧陆思想传统中,马赫、齐美尔、和埃利亚斯的反思性观点,或许影响最大。这两大思想传统都力图摆脱笛卡儿的“心-身”二元论立场,把心智和肉身看作是基于同一类因素的“现象”。在诸家学说当中,我认为,马赫思路的影响至今未衰。经过了怀特海晚年著作(《过程与实在》)的传播,由马赫、伯格森、詹姆士开创的这一思路,在当代被称为“发生哲学”。
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极大差异,中国文字塑造的中国人的“身-心”思维,是一体化的。惟其如此,中文以同一汉字“心”表示情感的、身体的、和智能的心,并且中国哲学传统的主流是心物合一的从而始终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区分。
为说明我们人类在开发自己的脑的能力方面处于多么落后的局面,我邀请读者仔细审视下面这组大脑神经元网络图(引自1998年出版的卡特的著作《心智地图》,英文版):
(请看下页的图):
左图是新生儿大脑的神经元连接状况,即神经元之间连接纽带的分布,可称为“疏松”。当儿童发育到六岁左右时,如中图所示,脑神经元之间连接纽带的分布表现出的错综复杂,可称为“密集”。最后,大约在十岁以前,见右图,儿童的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再度变得“疏松”但远为“粗壮”,这是经过了学习和建构了对世界的基本想象方式之后的疏松,故而,可称为“成熟”。从疏松到成熟,为了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如农民为庄稼间苗一样,大自然也给脑内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纽带间苗。
这样,儿童大脑在六岁的时候,大约已经获得了超过成人两倍的神经元之间连接纽带的数量。在其后的“间苗”期间,儿童的认知结构、情感结构、人格结构,这三类基本的、决定了人生命运的心智结构,就开始“定型”——除非发生特别深刻和震撼性的个人事件,这些基本结构不会有很显著的改变。用中国民间流传着的看法表述,就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依然记得自己儿童时期的“特异功能”,最常见和典型的,是“看见声音”和“听见色彩”。脑科学研究表明,儿童在十岁以前的“间苗”过程中,视觉区(枕叶)和听觉区(颞叶)交界处尚未定型,这使得许多儿童具有音乐天才和绘画天才的那种对声音和色彩的直觉能力。随着“间苗”过程接近结束,我们便逐渐丧失了这些特异功能,成长为普通人了。
当然,我还可以列举与上述类似的人脑在其他方面的直觉能力。不过,我们所处的局面已经很明显:我们原本可以拥有强大得多的直觉能力,却因为自然演化和生存压力,不得不放弃。认知考古学者和演化心理学者已经达成共识性的看法:今天决定着我们的认知结构、心智结构、和情感结构的基因交互作用过程,定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那时,我们人类尚处于“狩猎与根块采集”的生产方式中,面临着与今天完全不同的生存压力和社会交往环境。可惜,与文化的演化相比,基因演化异常缓慢。今天,当人类极端需要把思维能力上升到新的、以直觉为主要形态的层次时,她却发现自己大脑的基因过程还停留在新石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