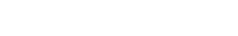胡列雄,男,65年生于安徽。93年五道口货币银行学专业毕业,先后任职海口农行国际业务部,北京金新经济研究所,深圳发展银行北京分行等。现居昆山,职业投资人。
老舒,名幼冬,字幼冬,外号幼冬。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1989年考研期间。偌大的安庆考区,不过7,8个人,3天考下来,彼此便熟了。老舒精瘦,戴着一副深度眼镜,见人主动打招呼,声音大,中气足,一见面便知他是性情中人。考试时,我很多题不会,百无聊赖,四下张望。老舒在我后面,但见他奋笔疾书,笔走龙蛇,一派成竹在胸的模样;江腾飞在我左侧,我看得真切,字老大,考卷写得满满当当的,一副丰收的景象。果不其然,他俩金榜题名,老舒保留学籍一年,我名落孙山,回农行继续我的稽核员生涯。
1990年我又一次参加研究生考试。这一次我也尽量写得满满的,自我感觉良好。可通知书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期间我照常下乡,在辖区信用社盘盘库存,和同学喝喝小酒,打打小牌。忽一日,我下乡回来,自行车还未停稳,营业部汪会计鬼叫也似的:“老胡快来接电话,都找你一天了!”我一接电话,脑瓜子就嗡嗡的:“恩(你)跑laiai(哪里)去子,到处都找不到恩。”那头声音很急,蹩脚的安庆土音,不时冒出几句粗话,像是老朋友似的。谁呀?我一时想不起来。对方随即作了自我介绍。哦,老舒!怎么想起来找我?原来,那1年,安徽有7人考取五道口,学校就派一个老师来合肥组织复试(面试)。那位漂亮的女老师(后来听说是小师姐)联系到了6位,开始找第7位(我就是,没人通知到我),就着落在老舒身上。老舒还在安庆人行。那时联系方式只有固定电话,我不在家,他只好守着电话,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地打。我一回来,他电话就如影随形追过来:“恭喜老兄,研究生考试初试通过了,赶快到合肥参加复试!”老舒的话天际边过来,飘飘渺渺,我听得恍恍惚惚,晕晕乎乎,梦游一般!
好在,梦想照进了现实!老舒,贵人也。
我到合肥时,其他人快面试完了。老舒陪着师姐,鞍前马后,殷勤备至,俨然助理考官也,见我过来,便把我介绍给师姐,小师姐笑靥如花,对我勉励有加。面试完,老舒跟我说,就我各科无缺陷,大约是表扬了,我不禁把胸挺上一挺,接着他又评价我的面试作文,两个字:霸气!几个意思?是褒是贬呢?那时我跟他不太熟,没好意思问。记得那篇命题作文叫《我是如何准备研究生考试的?》,倒苦水呗,无非是,怎样怎样艰苦,如何如何努力,于我,真情实感,一气呵成。结尾一句是:我,终于挺过来了!若有问题,就是它了,难道我骄傲了?
一直想问他来着,却被五道口新鲜生活所陶醉,渐渐忘了。
两年多的五道口生活轻松而愉快,丰富且多彩。
1990级三、四十号人住在那两层小楼的后楼的左边,教室就在1楼。我们生活、学习井然有序。
老舒和我成了同班同学。他性格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说话做事都不太讲究,他自己不知,别人怪他,他也不介意。我和他交往多,有时也被他烦得要死。譬如说抽烟。我们好几个人都抽,他抽得较凶。偶尔的互相敬一下,礼尚往来,一团和气,绝大多数时候各抽各的。他有烟时倒也慷慨,挨个发,不凑手的时候多,就找人要。他来我宿舍串门,看到我桌上有烟,拿起1支就叼嘴上,把手一伸:“火呢?”完全不拿自己当外人。我白他一眼,颇为无奈。下次看他过来,我便把烟悄悄藏起来。现在想起来,是我小家子气了。他就那样,并非故意占人便宜。
我和陈光明、杨俊川住一起,我们宿舍差不多是明星宿舍,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个重要因素是围棋。光明兄是围棋高手,隔壁的万跃楠也是高手,据说他俩都有业余初段水平,碰巧他俩还是大学同学。学校曾组织了一场围棋比赛,他俩代表1990级各赢了一盘棋。晚上或周末空闲时,他俩便在我宿舍摆上一盘,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两个人刚摆上,不一会,一大帮人渐渐围拢来。老舒听到动静一准会过来,他本喜动,闲不住,刚刚围棋入门,心痒难搔。看客除肖世优和刘翔外,水平泛泛,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热闹,说不出什么道道来。老舒是例外,看的时候老是指指点点,也不管人家烦不烦他。
光明是我围棋启蒙老师,杨俊川、胡浩、程甲生、张锐、吴剑辉包括老舒都是在光明和老万的带动下学下围棋的。我和胡浩形影不离,同是安徽老乡,被人戏称“二胡”。“二胡”围棋水平相当,菜鸟级,经常下,偶尔斗得性起,谁也不服谁,一下一晚上,第二天爬不起来,逃课去也(切莫告诉黄永鉴主任)。
我不太喜欢和老舒下,不是嫌他水平低,他老悔棋!和他下时我和他总是约法三章,落子无悔,放在虎口也不行!我知道他下棋有两大“利器”:一是断,只要看到断点,他第一时间就断上去。此时我故意卖个破绽,他一断我就将他夹住或者征吃。有时看到两块活棋,他也去断,我忍不住出言讥讽,他想悔,我死活不让。二是打“劫”,他才不管打“劫”值不值,有没有“劫”材,能否打赢。造“劫”时,生怕你看出来,他故意引诱你朝别处看。造出“劫”后,他洋洋自得,那份得意,全写脑门子上。我赢他时多。偶尔他赢一盘,一阵狂喜,输了呢,满不在乎,临走,拿我一支烟,点上,喷出一口浓烟,嘴里唱道: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啦----,音拖得老长,韵味十足,在走廊里久久回响。
五道口毕业后我们虽各奔东西,还经常保持联系。我想离开海南时找过他,他满腔热情帮我张罗,只是阴错阳差,没能成功。我在深发展时,他要找校友提携我,吓得我忙不迭地摇手。我有次到深圳,在他家楼下和他一起喝茶,聊得入巷。他还是那样没变。他邀我下了一盘棋。这次,他成功断我棋,擒杀一条大龙。他高兴极了,当我的面在电话里口沫横飞地和人吹嘘。他以为自己棋艺精进,其实只是我好久未下了,手生而已。
还有一次他来北京,非要请同学们吃饭。按道理,他是客,我们是主,应该我们做东才对,可他偏不。席间,他兴致很高,酒喝不少,话滔滔不绝。从他的话里我知道他来北京好几天了,应邀和人打麻将,赢了好几百大洋。赢了几百大洋没什么骄傲的,关键在于赢的是某位大家都知道的业内大咖。他说人家业务水平很高,麻将水平很次,瘾还特大!非缠着他。财喜送上门,不要都不行,说完他乐不可支。这才是他坚持要请客的真正原因。
后来我和道口同学见面,有时聊起老舒,说起他的一些往事,说一次,乐一次。有位同学这样评价老舒:五道口一个有趣的人。
诚哉斯言!
谨以此文纪念老舒,怀念老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