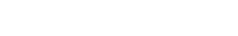1988年春节从牙龙湾给她买的项链
她的姓名叫郑炎英,但极少有人知道。
上世纪初出她生在重庆江津乡下,因为重男轻女,出生后被遗弃在田边。数九天寒,几小时后已冻得发紫,哭不出声了,幸被吃斋念佛的大伯娘看见,捡了回来。
贫苦中长到22岁,嫁给了一位青年农民,育下两儿一女。丈夫比她小两岁,夫妻恩爱,生活似乎有了温馨。不幸的是丈夫一天劳作全身大汗后被淋了冷雨,发烧继而转为肺炎,很快离她而去。那时她还不满28岁,拖着三个小孩,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小儿子送亲戚后,因穷病交加,3岁多就夭折了。不得已她又冒着烽火带着一儿一女从乡下到重庆觅生,女儿又在日寇重庆大轰炸的较场口惨案中丧生。
长子成了独子,成了她唯一的希望。怕儿子受气,所以她年轻守寡,到重庆利群银行汪协理家当佣人,抚育儿子长大。
熬到了日本投降,熬到了新中国成立。新生活在眼前展开。儿子当了工人,当了团支书,又当了公方代表。她也进扫盲班识字,白天在中药材公司当工人加工药材,晚上到街道纳鞋底支援抗美援朝。随后又是轰轰烈烈的噩梦般的大跃进,是饥饿的1961、1962年。灾荒中她被辞退,回家当家庭妇女。1963年,我呱呱坠地,她很高兴,说:“长孙当幺儿。”对我疼爱有加。
从小我就和她一个床睡,直到9岁左右。她摸着我的小脚丫说她小时缠脚的痛楚。我7岁上小学起她就鼓动我找女朋友,叫我把女同学带回家让她看。
在我的印象中,她一直有严重的哮喘,入冬即发,夜里拉风箱似的不能入睡。我牵着她的手一起去拔火罐、刮背、针灸等等,还用了诸多偏方,如喝我小弟的童子尿、吃红茶菌等等。还清楚地记得7岁时陪她去远郊的一个部队医院看病,要经过一座吊桥,第一次我不敢过,她牵着我,第二次我跑在前头,第三次我觉得好玩有意晃来晃去,她站不稳,抓着吊绳干着急。
家务事她全包了,每天早上六点就去公园和老太太们一起练甩手功,顺便捡些干树枝回家烧灶。有时一大早就去排队买菜买豆腐,记得一次她天没亮去排队买不要票证的肉骨头,到10点多钟,天降大雨,水漫过了街沿,父母又上班去了,我趴在二楼的窗口,看她穿着阴丹士林蓝的中式对襟衣服,在雨中一拐一拐地挪着小脚回家。
我们三兄弟经常惹她生气,也许听力不大好,她的呵斥声就很大,我就用刚从书上学的成语大惊小怪来形容她,她听了更火,说你们才是妖精妖怪。
三楼的大毛哥哥因患心脏病去世了,他父母是“右派”,在农场劳改,家中没有大人,她张罗给逝者穿衣收拾。那时乡下穷,每年春节前后都很多穷亲戚到我家里来寻求救济,一次妈妈因为捉襟见肘的无奈给了一个亲戚脸色看,亲戚要走,她哭着拉住不让走,我在旁边跟着哭。那时我家住在一个有十来户人家的大杂院里,收信收电费等极琐碎的事,她总是认真地揽下。
她识字很少,但表达却很精彩,看见我们小孩打闹跑热了脱衣服,她就说:“你们和唱戏的一样,一会儿穿了脱,脱了又穿。”形容我们偷懒,是“老者唱戏,光说不做。”冬天她给我们唱“一九二九,怀中插手;三九四九,冻死老狗;五九六九,隔河望柳……”
她很精神,头发永远梳得光光,衣服、被单洗了都要用米汤浆的挺括,她很瘦,但眼睛明亮,顾盼生辉。

我18岁生日时的全家福
她笑起来时,皱纹一圈圈在脸上波浪般展开,眯了双眼,极慈祥的样子。
有时我耍小心眼,玩小花招被识破,或者与弟弟们争小利益斤斤计较互不相让时,她总是摸着我的头,看着我和蔼地说:“三贫三富活到老,做人还是忠厚老实一些好。”
我从小在父母面前没撒过娇,总是很累地按要求做两个弟弟的榜样。但在她面前却完全放松,上大学了,读研究生了,回家的第一件事也是找她撒娇。回家轻轻放下行李,偷偷从背后捂住她的眼睛,她很高兴:“我的大蛮回来了。”
小时犯了错挨父母打骂,她总是挺身护犊,不问缘由。又呵斥父亲,小时你干了几多错事,使父亲心虚气短,败下阵去。
她的眼睛明澈,对我真是无保留地信任,信我所干的,干我所信的。我的成绩先向她汇报,我的喜悦先与她分享。
她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最好的赞扬来自她口,最大的温暖来自她手。她的鼓励使我不敢懈怠,她的期盼使我自惭形秽。
由她我常想到我们的教育,父母之于子女,老师之于学生,上级之于下级,是不是该少一些苛责,多一些鼓励?冀可使后生少些许自卑,添几分自信?因为温暖来自宽容,最大的动力和责任来自无保留的信任。
初三时搬家到四楼,她就少下楼。后来我们三兄弟都上大学了,她更渐渐足不出户。每次寒假暑假回家,我们都搀扶她上街,去看电影,去照全家福,那是她最高兴的时刻。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她的眼睛不复清澈照人,她的牙掉了很多,嘴瘪了,只能吃稀软食物。
1984年我大学毕业,第一次领工资就给她做了一身新衣,第二月给她镶了一口新牙。有新牙她吃得多一些,身体也好一些了,白发甚至转青。
1990年我研究生毕业,辗转深圳,海口。每年只有春节回家十来天,而她冬天哮喘卧床的时候居多,但挺过冬天又能下床。
1991年春节我写了第一本书《中国股票市场》,她看着书上我的照片高兴得合不拢嘴。
1992年春节前,我回到家里。她依旧卧病在床,一天下午3点多,我在书房看书,妈妈在忙过年的家务。
突然,妈妈惊慌地推门叫我说:“奶奶可能不行了,你快看住她,我去叫医生。”我放下书本,抱住她,她闭着眼睛,很安祥但已没有气息。我呼唤,没有回音,我抚摸她的身躯,正由温热逐渐到冰凉。
之后是悲伤,是守灵,是追悼,是送葬,似乎在她被推进炉火熊熊的焚炉的一刹那,我才明白她真的已离我远去,一去不回,背后再也没有她殷殷的目光。
1992年春节刚过,恰小平南方谈话后,海口是如火如荼的疯狂。办完丧事已订不上重庆直飞海口的机票,傍晚,飞广州的机舱外残阳如血。连夜乘卧铺车去海口。车上放着张行的歌:“你曾经轻轻牵着我的手,踏过草地走过山坡,你说那青山永远挺立,绿水它不会停留。人生需要努力和奋斗,不要向失败低头……为何你走的匆匆,来不及告诉我,来不及告诉我你就走。人生的道路永远无尽头,经得起失败的折磨,为何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牵不到你的手。”我一直排斥流行音乐,而此时此刻的歌曲却排山倒海地把我淹没,在随后的无声的深夜里,我泪流满脸。
回想自己的童年,回想她的点点滴滴,黑暗中我任凭泪水纵横,却不抬手一揩。
以前从书报上电视上见过几多死亡,一些情节,一些数据,一些画面,似乎无动于衷,事不关己。直到此时,最疼我的人走了,当她的音容笑貌成为记忆,当再无处可以撒娇,当再无慈爱的眼光把我追随,我才痛入骨髓地切切实实地理解“死”的含义,才真正知道生命是多么脆弱。
我的人生观从此有了大的转变。
父母按她的生前愿望,把骨灰带到乡下与爷爷的墓合葬。1998年我从北京到重庆工作,春节携妻回乡扫墓,买了很多鲜花瓣洒在她的坟头上,又放了长长的爆竹以驱秽气,又用红漆仔细地描了墓碑上的字,以寄哀思。
前些年时常梦见她,梦中她和我说话,她影影绰绰地走动,她目光拳拳地看着我……仿佛她还陪伴着我现时的生活。
记得还在我十多岁时,每每冬天看到她喘得接不上气,就计划在她去世后一定写篇文字悼念她;我曾想过带她乘飞机去看大海;曾想过戴上博士帽让她坐在中间照全家合影;曾想过在她的葬礼上点一千支蜡烛,不放哀乐而重复放贝多芬《第三交响乐》第三乐章中激昂向上的一段……然而这些都没有实现。
最近翻看她年轻时的照片,我似乎第一次惊讶于她的光艳,在发黄的颜色中,散发着青春的光芒。如一首诗所说:“她镇定而坚决,象经过过滤的早晨,昂扬散发着芳香;像一湖水宁静而生动,我知道她曾是天上的一颗星,从春天开始,再到云飞烟灭。她的眼神中没有一丝惊慌,她已经永远不会再来,只是将声音留给了时光。她完成了一朵花的展现,一粒种子的过程,像一片云和一个精彩的梦”。
“我曾赤裸在你怀中,那么幸福;我曾试图抓住你的双手,那么徒劳;我曾在你的掌心站立,为了飞翔……自你走后,我就无家可归,自你走后,这世界已面目全非;而你凝固在相片中,仿佛时间的人质;我甚至不敢多看你一眼,无数次,我忘记了钥匙,却揣着你的嘱咐出门。”
好久她没来入梦了,有时我想自己是不是被生活打磨得麻木不仁了,是不是开始老了,甚至有了“杜鹃声里斜阳暮”的寂寥之感。
昨夜,我又梦见了她,梦见她在对我笑,我最熟悉的她慈祥的笑容,猛然醒来,看见窗外点点的繁星,整个天空都是她灼灼的目光在凝视着我。
“还是忠厚老实一些好。”耳边又轻轻响起她亲切的声音。
她是我最亲爱的奶奶。
今天是正月初十,是她的百岁生日。
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因为丈夫姓胡排行第四,年轻时人们叫她胡四嫂,又叫胡四婶,又胡四婆,胡婆婆。为别人,为家庭她一生辛劳。她默默地奉献自己,从未希冀回报。她是旧时中国普通女性的一个缩影。然而,正是这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母亲和奶奶,给了我们温暖和力量。她们永远不会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她们是平凡甚至是渺小的,渺小到几乎没人知道她们的姓名。但她们又是伟大的,因为她们给了我们无私的爱,她们是我们漂泊心灵最后的归宿。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我的思绪能达到您的灵界吗,奶奶?人生能有多少路程,那些路程您牵着我走过;人生有多少日子,那些日子我曾依靠在您身旁。如今没有您在,我的伤痛有谁抚慰,我的辉煌由谁共享。
如果真有来世,我愿再做您的孙子,讨您更多的欢心,慰您更多的荣光。
安息吧,奶奶。
读者评论:
真的为你对奶奶那种深沉真挚的情感所感动。细腻的情景描写,如泣的情感倾诉,难忘的生活诙谐的语言,特别是奶奶让你从7岁就开始找女朋友,还让你带回家奶奶为你把关,让人眼睛有些模糊。真的,拜读后让人感慨万分,善良的中国妇女,在她老人家身上凝聚着传统美德和纯朴人性。好文章,好文采。
平凡质朴的语言,近似白描的刻画,读来叫人泪湿眼眶。真实感人的场面,仿佛置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