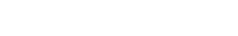高善文校友
正确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运行的内在逻辑,从而降低预测失败的概率。
我想先讲一讲我个人对研究方法的一些想法和体会。这部分陈述在我看来是异常重要的,尽管它没有实际的内容在里面。为了把这部分讲清楚,我给大家讲几个故事,也会使大家听起来更轻松。
1.非洲蚂蚁如何找家?
在几十年以前,生物学家很热衷于使用进化理论来研究生物的行为。在这种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发现非洲沙漠里有一种蚂蚁,这种蚂蚁找回自己巢穴的行为非常奇怪。
在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正常的条件下,蚂蚁要找回自己的巢穴,主要的办法是在它们离开巢穴的时候,沿途留下很多气味。这样,等到蚂蚁要回家的时候就会循着气味回家,因为蚂蚁是没有视觉的。知道这样一个原因的方法是很简单的:在蚂蚁经过的沿途放几个樟脑球。一般的话,蚂蚁就会迷路。
但是,科学家发现非洲沙漠里的这种蚂蚁,实际上不是依靠气味来识别路途的。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大家对这种蚂蚁如何找回自己的巢穴非常感兴趣。
当时,为了解释这种蚂蚁是如何找回家的,出现了很多竞争性的理论。其中一种理论认为,在这种蚂蚁体内,有一种计步器。当蚂蚁离开自己巢穴的时候,它的计步器就开始工作,统计蚂蚁的步数。然后,当蚂蚁找回家的时候,计步器可以反向工作。当计步器清零,蚂蚁就知道已经到家了。
从研究的角度,我们把迄今为止的这个案例总结为两点:
我们看到研究的第一步是观察现象,提出问题。他观察到的现象就是蚂蚁回家,提出的问题就是这种蚂蚁回家很奇怪,那它是如何回家的呢?
第二步就是提出理论,做出猜想。为了解释所面对的现象,我们要提出一个假说,提出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在逻辑上要能够自圆其说,要能够解释所面对的现象,这是研究的第二步。
但是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间,人们不知道这个假说是不是对的(就是蚂蚁体内有计步器的假说)。
我以前曾经问过很过很多面试的学生和实习生,如果现在把这样一个假说抛给你,要试图知道这个假说是不是对的,怎么办呢?
不少学生的第一直觉是把蚂蚁解剖一下,然后用显微镜,用生物学的方法来寻找计步器在哪里。其实稍微简单地想想就可以知道,这种办法在操作上是非常困难的,是几乎不太可能成功的。
因为计步器作为一种假说,很难跟具体的生物器官去对应起来。即便你能够对应起来,这种器官的运作在解剖学的意义上也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始终不知道这种假说是不是对的,它毫无疑问是一种引人注意的、很有趣的假说。
前几年,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生物学论文,这篇论文就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计步器的假说是否是正确的。
它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以现在的眼光看,办法很简单,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不知道这些办法。
它的办法是把这些蚂蚁捉来,分成两组。把第一组蚂蚁的腿截断一半,接到第二组蚂蚁的腿上。这样第一组蚂蚁的腿就缩短了一半,第二组蚂蚁的腿就延长了一部分。这些是在蚂蚁离开家以后非常快速的完成的。
如果计步器理论的假说是正确的,从这个假说出发得到的预测是,腿被截掉一半的蚂蚁在往回走的路上,在中途一半的时候就开始表现出找家的行为,主要就是开始团团转;而腿被延长的蚂蚁,会跨过自己的巢穴,继续向前走可以计算的距离,然后才表现找家的行为。从这样的假说出发,理论上可以做出这样的预测。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用实验证据的方法来看看这个预测是不是正确的。
这篇论文能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假说居然是正确的。蚂蚁找家行为的表现与这一理论的预测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研究的第三步和第四步。
如果说研究的第一步是观察现象,提出问题,第二步是提出假说,提出理论,那么研究的第三步就是从假说和理论出发,从其内在的逻辑出发,去提出一系列的预测。这一系列的预测本身是基于理论的内在逻辑推演出来的。
研究的第四步就是有系统性地搜集经验、事实和证据,并把这些经验、事实和证据同理论的预测相对照。如果理论的所有预测都能够和经验事实一致起来,那我们就接受这个理论;如果理论的预测和经验事实不一致,那我们就推翻这个理论,去寻求一个新的理论。
这就是我们迄今所知道的所有科学研究的四个步骤。这四个步骤是缺一不可的,关于他们的重要性,我们再举另一个例子。
2.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得更快
在古希腊时期,那时的人们很喜欢辩论。为了支持辩论技巧,一部分的人发展起了非常发达的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在此后上千年时间里的发展水平都没有超过古希腊。形式逻辑在那个时代的顶点应该是欧氏几何。
欧氏几何基于非常简单的假设,就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一条直线”。它基于如此简单的一条假设,就可以推演出非常庞大、非常密实的命题体系。
古希腊学者在那个时代就试图论证“地球是圆的”,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证据,他们还以几何学为基础去估算地球的周长。即使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估算成就也是很了不起的。
我们想说的是,任何一个理论都必须有逻辑,而它的基础就是基于古希腊时代的形式逻辑。在数千年以前的古希腊时代,大约跟中国的孔子时代差不多,希腊人的逻辑就已经非常的发达,远远高于中国先哲的水平。
但是我们也知道,古希腊有一个先哲亚里士多德。他的庞大的理论之中有很多命题,其中一个广受瞩目的命题是: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得更快。这个命题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非常明确地阐述。而我们现在清楚地知道这个命题本身是不对的。
但是,从亚里士多德提出这个命题一直到伽利略时代,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没有人公开地、严肃地去质疑这个命题或这个预言。为什么呢?因为在漫长的时间里,人们不知道做科学研究的第三步和第四步。
亚里士多德观察到羽毛比石头下落得更慢,观察到一个现象,他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的更快。这已经是一个抽象,是一个理论。但是这个理论是不是正确的呢?
他需要第三步,以这个理论为基础做出预测,然后是第四步,用可控的实验去验证这个预测。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一直到伽利略时代的漫长的时间里,人们不知道为了取得知识和理解上的进步,第三步和第四步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那漫长的时间里,科学本身并没有诞生。直到伽利略和牛顿时代,人们才认识到,理论不但需要逻辑支撑,还需要对世界做系统的观察,并用这些观察来验证理论的预测,在验证的基础上推翻一个理论或者接受一个理论。
爱因斯坦曾经讲过,现代科学的诞生是一个偶然。这个偶然来自于两种思想的碰撞和汇融。一种思想是形式逻辑。从现代对文明史的回顾来看,只有在古希腊提出了非常发达的形式逻辑。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源头就是实证精神。所谓的实证精神,就是对事实有系统的搜集、测量和记录。
只有当形式逻辑和实证精神这两种思潮交融在一起的时候,科学在欧洲才大放光芒。从伽利略时代到牛顿,到达尔文,到麦克斯韦,到爱因斯坦,无不是遵循这样的方法,将科学推向更加昌明的地步。
3.光线是可以弯曲的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本身在数学上,在思想上,毫无疑问是异常复杂的。但是他所做出的预测,他所做出的可以观察的、以前人们所不知道的预测,却是惊人的简单。
比如,一个非常重要的预测是:当光线通过重力场的时候,光线本身可以被拉弯。这个事实以前人们是不知道,并且是无法想象的。而这个在现代天文学的观察上一般叫做“重力场的透镜效应”或“爱因斯坦透镜效应”。
以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为基础,他所能做出的预言是什么呢?爱因斯坦本人严密计算出来的预言是:当发生日全食时,太阳的光芒完全被月亮屏蔽。在这样的条件下,太阳背后的恒星所发出的光经过太阳的重力场时被拉弯,照射到了地球上。这个时候人们对这颗恒星位置的计算,同太阳在其他位置时的计算有轻微的偏离,而这个偏离的大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1918年,英国的远征队分别在地球的不同地方对这一预言进行了观测,而观测的结果与爱因斯坦的预言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广义相对论获得广泛支持,爱因斯坦成为世界名人非常关键的实验证据。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科学研究的四个步骤是缺一不可的,科学研究本质上是实证精神和形式逻辑的结合。
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然之
如果我们回过头看中国三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会看到中国人既没有实证精神,也没有形式逻辑。在中国大量的史料中,我们看的纪录是,皇帝今天晚上宠幸了哪位妃子,名字叫什么,我们看到的是韩信在月下策划政变,最后没有成功。我们没有看到对世界的运行做出的有系统的测量、观察和记录。
中国的先秦时代也有很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也推动了逻辑的发展,其到达的高度中国人在后来再也没有到达过,但是它跟古希腊的形式逻辑相比是不在一个量级上的。
在朱熹或是更晚的时代,知识分子都醉心于解读古代的典籍。这种解读首先沉迷于对定义的辩论。比如对论语的解读,首先沉迷于这句话在字义上如何解读,如何定义,而没有严密的逻辑推演和合理预测。
举例来说,康有为如何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然之”呢?中国古代是没有标点的,这句话在很长时间里大家的解读是一样的,但是康有为提出了新的解读,认为原意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然之”,意思是“如果老百姓答应,那就这么办,如果老百姓不答应,就跟他们讲明白”。这个倒有点儿像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理想。但是包括梁启超在内,对这样的解读都非常的怀疑。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古代的治学方法:命题的本身没有非常清晰的含义,命题的基础没有非常严密的定义,命题的展开过程没有密实的逻辑,命题本身也没有提出任何预测。有时候即使提出预测,人们也不用系统性的观察去验证这个预测。
例如,在中医的著作中,关于生男生女在理论上是这样解释的:夫妇双方如果在单日行房,则生男;在偶日行房,则生女。这也是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做出了很重要的预测,但是你没有看到哪个中国人去系统性地搜集事实来验证这个理论。
所以中国人在漫长的文明史中既没有形式逻辑,也没有实证精神,所以中国自始至终没有科学。但中国文明居然延续至今,也算一大奇迹。
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么遥远的孔子时代讲起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既没有形式逻辑也没有实证精神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即使是洋务运动和五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的思想在中国开始广泛的传播,但是在骨子里,中国学者仍然非常深刻地缺乏实证精神,非常深刻地缺乏形式逻辑。余续所及,影响很广。
5.引力与温度无关
接下来我们对研究做第二个层面的展开。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呢?研究的对象在本质上是讨论因果关系。那什么叫因果关系呢?因果关系本身需要一个密实的定义。
以我个人的体会来看,因果关系是对一个封闭的系统而言,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输入,也可以观察到它的输出。假设一个封闭系统,我们把它隔离起来,它有100项输入,我们可以看到输入,也可以看到输出。当这个封闭系统的99项输入都不变,只有1项输入在变化,这个输入的变化在输出层面所产生的变动,我们就说这两个现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之所以要对因果关系作这样一个密实的定义,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牛顿时代,牛顿本人研究了很多的现象,研究了光线色彩的构成,研究了潮汐,研究了地球围绕太阳运动和月亮围绕地球运动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牛顿理论本身,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并不是他在数学上多么了不起,尽管他在这个领域也非常了不起。
我们想说的是,地球与太阳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依赖于太阳是由什么样的元素组成的,不依赖于太阳的表面温度是什么,不依赖于太阳本身的密度有多大,只依赖于太阳的质量和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而与太阳很多其他的属性,都是可以屏蔽和隔离开的。这本身是个奇迹,使得我们在研究地球和太阳相互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忽略太阳的物理构成,但是依然可以把两者的作用关系理解的非常清楚。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物理学研究的世界在原则上是可以隔离的。你可以把太阳的很多属性隔离掉,但是仍然把这个系统研究得很清楚。而当人们在研究更现实的物理理论的预测时,进行的都是可控试验。比如说伽利略,把两个铁球,一个20斤,一个10斤,从同样的位置放下去,人们看到它们同时落地。这个本身是可控试验。可控试验意味着你可以严密的控制输入。或者,在研究天体物理学的时候,并不是可控试验,但是这个世界的研究在方法上,在原则上,它居然是可以隔离的。这个使得在研究因果关系的时候,研究过程变得更加容易。
为什么经济学的研究在这个层面上非常的难?为什么生物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人体的研究,非常的难?为什么现代医药的研究非常的难?因为这个系统在原则上在方法上是很难隔离的。它不能够像研究地球与太阳的运动一样,把太阳的表面温度隔离掉。
比如在生物体的层面上,一个普遍的现象叫“代偿”,就是说如果你某一项生物机能非常的不发达,一定有另一项生物机能非常的发达。“代偿”很可能跟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的竞争有关系,但是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人体在研究上是不能简单隔离的。一个系统的调整在另一个系统之中会引起非常复杂的反应,这些反应又会倒过来影响你原来研究的这个问题,而且这些过程本身很难理解清楚。
所以,世界上有那么多杰出的物理学家,但是在经济学、社会学、或者医学等等领域,为什么缺乏物理学那样伟大的成就呢?我们可能对这些领域的很多学者不是非常熟悉,但未见得是他们不聪明。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处理的这个体系在方法上,也许人们需要寻找新的方法,至少简单隔离法和可控实验的研究方法是很难适用的。
6.雄鸡一唱天下白
我们都知道在经济研究中,对经验数据的处理,通常只能得到相关关系,但是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有很大的不同。
我先举一个例子,中国唐代有一句诗叫做“雄鸡一唱天下白”。这句诗描述了一个观测,有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公鸡叫,第二个现象是天亮。他还描述了这两个现象之间的联系,就是公鸡叫稳定地领先并预言着天要亮了。所以这是一个命题。
从这个描述之中,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两种现象至少存在着非常紧密的相关关系,而且公鸡叫是稳定地领先于天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鸡叫是天亮的原因。
我们如何知道公鸡叫不是天亮的原因呢?从这个命题本身,从他们密切的相关关系,从公鸡叫的领先这些角度,我们都是无法知道的。我们能够很幸运地知道这一点,需要其他一些知识。
这些知识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可以获得,第一个层面是现代天文学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告诉我们,天亮不亮和公鸡叫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接受现代天文学的这些结论,我们知道这是跟地球围绕太阳转有关系,而跟公鸡叫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些知识在我们刚才的数据处理系统之外,是一些额外的知识。如果没有这些额外的知识,我们不知道公鸡叫和天亮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第二个方法就是通过对鸡瘟的研究。鸡瘟使得大量公鸡都被宰杀,但是天照样准时的亮起来。这样一个自然实验清楚的表明他们之间不可能有因果关系。即鸡瘟这个自然事件导致公鸡叫这个现象被控制住了,没有公鸡叫了,但是天照样亮,所以说明他们之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鸡瘟提供了一个类似的可控实验。在这个系统中,把这个变量控制住,其他的结果是不变的,所以没有因果关系。
所以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之中,我们看到最近很多年以来,人们对自然实验的研究精力,比如一场地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比如通过双胞胎样本研究教育的影响……为什么人们去研究这些自然实验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自然实验比较接近可控实验,可以使人们接近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科学研究最终是为了逼近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