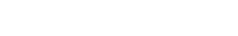此文已新浪原创上首发

五、病痛·离去
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和唐旭相约吃那年旧历年的最后一次饭,因为我跟他说,我在春节之前要离开北京回贵州去看望九十三岁的老娘。
那天我们相约的是金融街的加油站旁边的一个饭馆,当我见到他的时候,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的脸上长满了红色疙瘩,而且,整个脸显现出很沉着的紫色。当然,后来才知道,是吃抗癌药的反应。
“怎么啦,唐旭?”我吃惊不小的问。
“没什么,可能是吃药的自然反应。”唐旭轻描淡写地回答。
我怎么也没有往癌症这种病上面去想,因为像唐旭那样近乎于纯净的生活习惯,与任何对身体有害的东西都是绝缘的,在我的先入为主的意识中,肺癌是不可能找到唐旭的。
“要回家看父母吗?”
我知道他父母也八十以上高龄了,既然相信了他说的话,我也就保持语言界限,不再深问什么病,要吃反应如此之大的药了。
“今年有事不回去了,如果可能的话,也是年后再去了。”他这样回答。
在贵州遵义陪着我老娘过完了二零零九年的元宵节后,于二月十日回到北京,回来后只给唐旭打了一次电话,他说他比较忙,于是约定等他忙过一阵后我们再聚。
大约是到了二月底,有一天上海的付一书打电话来,问我知道唐旭生病与否,我说:“知道啊”,可是付一书又问:“知道得的什么病吗?”,我说:“这我就没有问了”。
“老侯,你也太有点大大咧咧了”。付一书用很沉重的口吻说了一句。
付一书说完话一瞬间,我敏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天啦,癌症!”。
我对癌症这种病,在情感上是极其敏感的,尤其是对患上癌症以后,病人的一切,包括全家人的生活、经济、亲情都将陷入一种沉重的境遇。对这些,我是再熟悉不过了,毕竟,在我的直系亲人中间,曾经有过三个癌症病人,两个已经去世,还有一个仍然处在生死边缘。
年前那一次相约吃饭,其实我就应该敏感到这个问题的,也许是我太过于相信:像唐旭那样有着纯正无瑕生活习惯的人是绝对不会罹患癌症的了。
我赶紧给唐旭打了电话,我们相约又去了“渝乡人家”。
“唐旭,你不至于如此脆弱吧,没有勇气告诉别人,你总应该有勇气告诉我啊?”一见面,我多少有些责怨地对他说。
“哪里嘛,那个时候,你不是一家人要回贵州过节吗?我是想让你好好回家过个春节,所以才打算着等你过节回来才告诉你的。”
“上一年你参加你们行里的秋季常规体检了吗?”我问。
“没有,那个时间正好在国外有一个讲学,回来后一忙,也就没有去。”
“唐旭,可能你是要为这个大意而付出代价了。”
我暗伤地对唐旭说了上面这句话。说到底,命运,就是一种我们自身无法改变的安排。唐旭说,在此前他一直都很注意,而且总是能按行里的规定,准时参加集体体检,而二零零七年是唯一没有按常规体检的一次。
那天吃饭的时候,我们讨论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件事是关于治疗方法问题。我们几乎同时说到关于保守治疗的话题,即不做放、化疗,而是通过中药、食物方式来完成癌病变与身体和平共处。回家后,我把我父亲去世后别人发给我的一个关于食物保守疗法的资料发给他。
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后来我和他一起中午相聚的时候,都约定好,他只吃素的,我呢,点一个肉菜,但为了不至于对他形成引诱,或对这种引诱给予一定的综合,每次都点一个相对清淡,但多少有些荤菜味的“排骨炖萝卜汤”,还约定好,唐旭只许吃萝卜,不许吃排骨。
当时的唐旭,因为并没有进行放、化疗,味觉仍然是很好的,所以,每次在大众场合吃饭,对他的食欲来说,可能都是一种考验。凡是我们单独在一起吃饭,看他那个多少有点馋的样子,有时候,我也会忍不住对他说:“偶尔吃一两块,没有什么吧?”。
“算了,老侯,那个癌症食疗清单可是你发给我的。” 每次他都忍了忍,还是没有向想吃而不能吃的食物伸筷子。
第二件事是关于是否继续上班的问题。他说他现在还在上半天班,行领导同意的,但是我说:癌症这种病,说到底就是免疫系统被破坏造成的,应该忌劳累。
“我想,工作就是一种精神,精神对于我的病,可能也是一种重要因素。”
我还是比较担心这种上班会导致劳累,因为我始终坚持认为,唐旭的病与他在研究局工作的那两年过于劳累有关。
在二零一零年一月唐旭去上海做生物治疗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唐旭除了进行“靶向治疗”外,同时还在山西一个姓梁的中医大夫那里看病。
“唐旭,我和你一起去山西那个中医大夫那里,好吗?”唐旭因为定期要去老中医那里看病,有一天我跟唐旭商量跟他一块去。
“你去干什么?”
“呵呵,哪天万一我也得了类似的病呢,正好借此机会把关系接上啊。”我半开玩笑地说,不想让他觉得我就是专门陪他去。
“瞎说,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吗?”
“说不定哟,这可不是我们自己可选择的,像我这种人,一身的不良生活习惯,得起病来比你更容易”。
唐旭告诉我,刚开始的时候,因他身体状况还行,都是开车去,但后来从北京到太原的动车开通了,坐动车更经济、方便,而且身体也免去了劳累。
比起开车到太原,也有不方便的一面,就是到了太原后,去那个大夫那里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我和他商量好了,我们头天住在太原,第二天早上要个出租去那个梁大夫的诊所。我和唐旭的这个约定,因为时间总是不合适,一直未能如愿。有一次他去之前告诉我,可我又正好有事,后来,有两次他又是跟别的人一块去,我就没有去了。
二零零九年的国庆节,我们两家人相约出去玩,在唐旭提议下,我们决定去马致远故居。
唐旭带路,车开进了门头沟的大山里,第一站在离马致远故居有约两公里的一个叫“韭园”的村落停下,这里已经被现代人按照马致远那首著名的《天净沙·秋思》,做成了小桥、流水、瘦马等雕塑。
唐旭带我们沿着韮园村头的小路一直往上爬,到了一个路边小庙,唐旭告诉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京西古道遗址。我算是比较爱好历史学的了,但与唐旭对历史细节的了解相比,可能还真的要“自愧不如”了。
“这就是历史上晋商驼队进京的主要干道”。女眷们去采植物了,我们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下来后唐旭说道。
“唐旭,是不是对山西特别有感情?”我随口问了一个关联问题。
因为还在二零零一年的时候,我们两家人一起开车经太原去平遥,在太原市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们一块去了晋祠,在晋祠,唐旭告诉我,太原是唐姓封地。
“你上次说了唐姓渊源后,我也追溯了一下我这个姓的渊源。”
“情况怎么样?”唐旭随口问。
“我们两人的姓,均源自唐叔虞,只不过唐姓是以国为姓,侯姓是以爵为姓。唐姓直接缘于唐叔虞封国,而侯姓缘于唐叔虞分封的一个被称呼为‘缗’的晋侯。”
历史上,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在位,周公摄政时期,将东征所得的唐国之地,封给了弟弟叔虞。即所谓“桐叶封弟”典故的来由。此后,姬虞(叔虞)即以封国为姓,改称呼为唐叔虞。
“呵呵,你的姓要大些哟,依次排下来,你是皇族姓,我却只是一个贵族姓哟”。我调侃地说到。
“我刚才看到一个关于‘落难坡大寨’的指示牌介绍,上面介绍说,南宋时期落难的徽、钦二宗曾囚禁之地,可靠吗?”我接着问。
“完全可能,按照宋代历史地图看,这一代原就属于金的地界,不过,现在为了抢旅游资源,杜撰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也很难说。”唐旭回答到。
整个韭园农庄由东落坡、西落坡、韭园、桥耳涧四个小山村组成。据传说,过去这里的人们主要以种植蔬菜为生,尤其以种植韭菜而闻名,因此而得名韭园,马致远的故居就在半山上的西落坡村。
我们在韮园村稍作停留后,继续开车上山,道路很窄,但路面很好。到了西落坡村,我们每人花了十元钱,参观了马致远的故居。因为有一条小河沟穿村庄而过,而马致远的故居正好在小河沟边上,倒也真的有点“小桥流水人家”的味道。进了故居的院落里面,枯藤老树,院里一匹尼塑的瘦马,我估计是后来的人们依据马致远那首著名曲牌人为做了这些景致。在我看来,当年马致远写作这首曲牌,以漂零流落意境构思,也未必就是以他的故居为据的。不过,如果这里真如唐旭所说,属于晋商古道,以所处地理特点看,的确多少有些与诗意吻合,只是未必意境就集中在这样一个小院落里。
看完马致远故居,我们去村东头的一个农家大院吃午饭。顺便也问了问这个村里是不是还有马致远的后人,也许是年代太久了吧,村里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我们提的问题。
农家院主人端上来是北京最地道的农家饭,味也是完全京味的,唐旭这时候的饮食已非常注意,肉菜是基本不沾的,不过看得出来,唐旭还是有克制自己的成份。
饭后,我们沿着村后的山村公路溜达,路边有柿子树,这个季节,树枝上已挂满了红红的柿子,而看着这些挂在树枝上像小灯笼一样的东西,真的会产生一种诱惑。
我和唐旭沿着公路漫步,这条路似乎很少有人走,问了问过路的村民,村民告诉我们,这条路几乎就是为后山上的一户人家单独修的。
这条山村小公路景致不错。最重要的是因为公路在半山腰上,位置高,可以远眺,山下的村庄和盘山公路可尽收眼底。
我们下山时,已是下午四点了,到达门头沟镇路边专门卖农家果蔬的市场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半。唐旭告诉我,他必须要停在路边打个盹。唐旭一直都有绝不疲劳驾驶习惯,记得二零零一年我们两家人去平遥古城的时候,到了石家庄,刚出收费站,在要入石太高速的时候,唐旭就对我说,他要在车上迷糊十分钟再走。
不过,这一次门头沟之行,从唐旭神色可知,他提出来要休息一下,已经不完全是出于 “绝不疲劳驾驶”了,而是真的出于不堪劳累了。
二零一零年元旦后不久,我和唐旭再次相约一起吃午饭、聊天,他告诉我,他要去上海做生物治疗,唐旭详细给我说了这种治疗的基本原理。其中细节虽然我也不是太懂,但至少知道是一种通过血液培养的办法,实现患者自身对癌病变产生抗体。
对于治疗,我和唐旭进行过多次讨论,但唯一忽略了的问题是:个体差异可能会导致治疗效果差异。就如当初我也鼓励他进行保守治疗,一半原因是生活中的确有与癌症长期共处的事例,甚至还有在保守疗法和食物疗法的治疗中,癌病变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的情况。另一半原因是,做放、化疗对身体的折磨是惨烈的,真的担心唐旭的身体会吃不消。在后一点上,我从我兄长的身上得到的感受太深了,因为他一九九零年查出癌症后,先是每半年要放疗一次,后是每一年要做化疗一次,在化疗期间,除了头发全掉了外,更重要的是会出现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的极度衰弱情况。
二零一零年的二月底,大约经历了一个月的生物治疗后,唐旭返京。二零一零年的三月初,在他再次出发去上海之前,我们相约在金融街小城知味吃饭。吃饭过程中,我问了他关于生物治疗的效果,从我这里而言,当然急切希望能看到这种治疗方法能在唐旭身上产生显著效果,那样,不仅唐旭可以从生命危机中解脱出来,而且还可以规避放疗和化疗带来的莫大痛苦。
唐旭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各项检验指标显示是正常的,肺部肿瘤阴影部分没有扩大。有关这个结论,是唐旭从二零零九年开始治疗以来,告诉我最多的好消息,因为一般的理解是:只要肺部阴影不扩大,似乎就是病灶有所好转的象征。
大约是二零一零年的三月十五日前后,也就是我们在北京一起吃饭后他返回上海不久的一天中午,我打电话过去问情况,唐旭告诉我说:他下肢不能动了,经检查是因为癌细胞转移到了胸椎上,压迫了神经,导致下半身不能动弹。
这个消息一下了让我懵了,情感触角瞬间感到了一种颤抖。我立即想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这可能将是癌症之外,甚至是比癌症本身还具有某种严酷性的病痛灾难,另一个就是最初确定的保守治疗方案,也许因为唐旭的个体差异而显示出了并不适应的问题,并且这个不适应所导致的后果,比一般的治疗不适应症要严重得多。
得知唐旭将于三月十六日进行手术。于是买好了三月十七日飞上海的往返机票,决定在他手术后去看他一次。
下飞机后,直接坐出租到了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除了唐旭夫人外,正好唐旭的姐姐、嫂子还有女儿都在。唐旭的姐姐,我以前并不认识,是二零零九年四月份,我、晓蓉、韩晋、丽莎、晓虹几位同学开车去看唐旭,并相约在峨眉山下与唐旭一块喝茶,然后我转道与唐旭一块去乐山看望唐旭父母时,在他父母家中认识的,这次在医院,算是第二次见面。唐旭的嫂子,我早就认识,相对熟悉。
唐旭手术后一直躺床上,我摸了摸他的腿,已然失去知觉,腿上已没有了肌肉,我真的不理解,数天前我们还在北京相聚吃饭,一切不都是好好的吗?才短短几天时间,神经压迫就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我去这一天,正好是手术后通大便之前最难熬的时间,我们到病房外回避了好几次,但唐旭仍然处在大便不能通畅的煎熬之中,看到他努力地控制住自己不让身体的难受感染大家,一下子又把我投进到我曾经有过的:在罹患癌症的亲人床边守候时,对亲人痛楚无能为力的无奈心境。
上海的专家建议对唐旭进行化疗,我也觉得,到这种时候了,化疗可能是可以采取的最好办法了,这样,至少可以避免无法预计情况下,癌症窜到更为致命的地方去。
这可能就是个体差异对一种治疗方案的适应水平的问题,而唐旭的问题在于保守治疗期间,也就是所谓“靶向治疗”期间,病变移动到了一个导致严重后果的部位,让唐旭在经历癌症病痛之外,叠加地承受了下肢不能动弹的痛楚。
下午四点,与唐旭及同来看唐旭的其他同学作别后,我离开医院去了机场。回到北京后,再打电话过去问情况,得知唐旭终于顺利通便,焦急的家人,甚至包括护士和大夫才松了一口气,当然,唐旭也才从术后身体无法通畅的痛楚中解脱出来。
从做完胸椎手术,一直在到二零一零年九月从上海返京,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唐旭一边在上海康复中心做下肢康复治疗,一边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进行常规化疗。
此间的六月七日,我约好万福燕,再次去上海看望唐旭,碰巧的是,陈润洲和吴婕两位同学也来看唐旭。唐旭仍然更多的时间要睡着病床上,但经过康复治疗后,已经可以勉强下地走动一下。
二零一零年九月初,唐旭回到了北京。一方面离家太久,想回家小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女儿要去英国上学,想要回来送送女儿,帮着指导一下女儿出国前的一些事务。
国庆节前,我从深圳回京,一回到北京,我就约了张晋生(同为刘老师的学生)去家里看他,发现唐旭几乎可以拄着拐杖走一点路了,这说明上海的康复治疗还是有效果的。
很快,国庆节到了,于是打电话问唐旭,国庆节有何安排,唐旭说在家里闷得太久,想出去走走。于是商量去什么地方,他也似乎有些说不清楚去哪里,后来是我提议:还是再去马致远故居,那里空气好,正好我也对道路熟悉。起初,唐旭说让我开他的车去,但由于要带上唐旭的轮椅,他那辆车后背箱空间可能比我的车要小些,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开我的车去。
去的那天天气并不是太好,虽然没有下雨,但是空气灰蒙蒙的,多少有些压抑。出了五环上六环的时候,我竟然不记得如何盘六环的立交桥了。这一次跟一年前那一次去马致远故居截然不同的是,那一次是我的车子跟在唐旭的车后面,我只管跟着就是了,而唐旭呢,因为去过多次,也很熟悉那段路,根本没有需要寻路的问题。可这一次不同了,包括我在内,车上的人都认为的盘桥方向是在六环上向南。唐旭甚至就没有否定我们的意见,只是说这样肯定不对,但指不出要怎样走。
于是,我把手机上的定位地图打开,可是卫星信号差,老是不能定位。经历了这样一个反复后,唐旭终于说应该如何盘六环那个桥。于是我又调过头来按照唐旭说的,重新盘旋那个立交桥。一路上,我还是有些犯嘀咕,总觉得方向反了,始终觉得我们要去的那个韭园村,应该在我们刚刚盘过来的那个六环立交的南面,而我们现在走的是向北的方向。
“看来还是唐旭的方向感是对的”。车一直行到了出六环到云峰上的路口的时候,我终于发现,还是唐旭是对的。
我说这话的同时,其实已经渐悟唐旭的反应已经不像一年前那样敏捷了。因为这条路对他来说,已不止一次走过了,他应该可以做出非常明确指示的,可这一次他没有,我们甚至还在六环的应急便道上把车停下来,等待手机上的卫星定位。
这一次,我们没有在韮园村停留,也没有再去看马致远的故居,而是直接把车开到上一次我们吃饭的那户农家。那天农户家里很冷清,也许是因为农户家的大院正在扩建的缘故。我们把车停在了离农户家门口约十米左右的路边上。从后背箱里取出唐旭的轮椅,然后推着是进了农家院。一条大狗在笼子里转来转去,看到我们进来,便大声吠叫。这可能就是冷清没有生意的一种表现,生意好,人多时,一条大狗不停的吠叫,谁还愿意来吃一顿不清净的农家饭呢。
跟主人家说了我们要点的菜有哪些,考虑到唐旭的饮食,我们点了大量的蔬菜。不过,也按照我和唐旭吃饭的老规矩,点了一份肉菜。由于农家院的女主人不在,要等她回来才能开厨,于是点好菜以后,我们推着唐旭沿着那条熟悉的山村公路去溜达,顺便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山村公路的两边长满了野菊,并且正值花儿开朵的时候,村民告诉我们说,野菊采回家,晾干了泡水喝,是一样很好的保健饮品,于是,家眷们便沿着山村公路两边,忙着去采摘去了。
我推着唐旭走到一个相对空旷、可以远远眺山下景致的地方,唐旭对我说:“老侯,我们在这里呆一会”。于是,我推他到路边上,出于安全,我手握着车把站在他身后,当然这样做,还可以尽量把车推得靠路涯一些,视野也就可以更开阔一些。
我们在一起共同沉默了长达十分钟之久,彼此都没有说话。我和唐旭单独在一起的次数多了去了,但彼此都没有说话,沉默如此之久,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此间,唐旭清了一次嗓子,我也多少有点为这种从来没有过的凝固氛围感到不自然,很希望此时唐旭能说点什么。所以,在他清嗓子那一瞬间,我感觉到空气会流动起来。可是,最终他还是什么也没有说,也许他的内心只是一闪而过的愿望,唐旭,毕竟是个理性十足的男人。
此时此刻,本应由我来打破沉寂,我其实也想到了是不是应该问问他,有些什么事需要在意外发生的时候由我来帮着处理。我这样想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由于在重庆,我和唐旭之间的一些相互悉知的事情,使得我跟他的父母、四叔、哥哥、嫂子等家人之间,有了一种比其他人更多的熟悉和联系。当然,在北京,我相信唐旭因工作会结交更多的朋友,但以本科同学为基础,并在家人之间也走得较近的,可能应该算是我了,所以,从理论上讲,如果唐旭有着某种思想准备,而且又觉得有需要拜托给第三人的事,我自认为我应该是唐旭可以信赖的人选。
※ ※ ※
不过,唐旭没有为后来的事,向我说点什么,事后一想,其实这符合唐旭“不党不争”的处事原则。
所谓“不党”,那就是,他总是能努力做到与身边的人都保持一种相对均衡、相互尊重的平行关系。在我觉得似乎唐旭会对我说点什么身后事的瞬间,我可能错误地认为,我和唐旭之间的同学、朋友情感,与他身边的其他同学和朋友有某种疏与密的区别。其实,现在冷静一想,这不符合唐旭的个性,也不符合一个优秀男人的行事原则。
说到“不争”,记得是二零零九年元旦前,在北京工作的金融七九级同学一起到青少年宫的“巴国布衣”聚会,那天温思渝也来了。那两天可能是因为常用药临时短货,老温说他有两天未能服药,所以手抖得比平常厉害。在讨论药的问题时,唐旭说了他服中药的经过,但关于中药有效性的证实问题方面,老温与唐旭之间意见和看法可能有所不同,产生了点小小争论。老温的观点与中医药一直不能在西方国家准入的理由是一致的。因为,如果对中医药进行物理、化学和分子检验,可能很难寻找到与身体被治愈之间的必然逻辑关系。
争论一直延伸到了东西方哲学差异,说到了公元前三世纪,欧洲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开始走向用物理、化学、分子的方法来实证世界规律,而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哲学,则开始向着唯神的黄老学说发展,于是才有了今天东西方科学发展上的巨大差距。我们中国的中医药,自然是中国祖先们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但物理、化学或分子的逻辑证明仍然是不充分的,所以对于病症的有效性,几乎可以说接近于一种玄学理论。
关于中医药的科学逻辑问题,我相信温思渝的哲学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比较一下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在抛弃早期宗教神秘化后,走上了实证意义上的科学发展道路。至于人文科学,那更不用说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欧洲文艺复兴,几乎一举解决了人类发展思维问题上关于:人与纯信仰之间谁为第一概念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才得以在欧洲逐步结束了“为自己之信仰而无端杀戮不同信仰之生命”的低人文时代,有关这一点,美国社会学家亨德里克·房龙的《人的解放》叙述得非常精辟。
不过,温思渝所说也有不完全尽然的地方。在说到医药科学问题上,由于是与千差万别的生命体以及生命意志相关联的理学问题,不能排除精神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真的就无需证明地解决了某种与病相克的问题。所以,生命科学,以及与生命科学相关的科学,均不会简单等同于物理学和化学,就像经济学不能简单等同于数学一样。
我们姑且不去判断唐旭和温思渝之间,各自的知识量与知识深度如何,仅就辩才而言,以老温的雄辩能力,是没有几个人能望其项背的。在一场有众多同学聚会的餐桌上,这种太理论化或者说无法让所有同学在情绪上参与进来的讨论,需要尽快结束才好,否则必然会冷了同学聚会的情趣。
在这个时候,唐旭主动地放缓了讨论的语气,并慢慢地从稍显激烈的讨论中退了出来,使一切又回到符合同学聚会的这样一种情感氛围中来。
※ ※ ※
以我和唐旭之间说话随便度而言,其实我也想到过主动问问他有什么事要交给我办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以唐旭的智慧,对俗世虚荣:应该是淡泊的,对生与死: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但是,我最终还是忍住了,一者觉得如果唐旭在此时此刻还不愿意说,那一定有他的道理。二者也觉得那么宁静的远眺,也许是唐旭自下肢不能动弹以来就没有过的了,我没有理由在此时此刻,去破坏他可以放开情感冥想的精神环境。
“唐旭,这可是风口上,还是不要呆久了,我们慢慢跟在她们后面,翻过山坳的那一边去,风可能会小一些。”
最终,我还是忍不住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打破了这漫长的沉寂。因山上太凉,轻微的山风对我这样的健康人,也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对于唐旭,可能就不那么简单了。
唐旭接受了我的建议,我推着他离开了那个远眺之地向山后走去。出乎我意料的是,过了山口后,山这边的风比山的那一面还大。
唐旭说:他想下来走走。我想也好,唐旭走一走,可以使身体发热,这样可以降低受凉感冒的概率。我推着轮椅走在唐旭的身后,看着他颤颤巍巍的步履,突然间想起了我那个经历过私塾学习,后来又做了私塾里教书先生的老父亲,他在遵义医学院放疗期间有感而作的一首七绝中的两句话:
“……沿院缓行人作杖,惧梯畏阶步踉跄”。这可能是我弟弟在医院守护期间,扶着家父在医院的大院里散步之后,家父有感而写的。
十月下旬从深圳回京,打电话问唐旭的情况,被告知在昌平与市区交界的一个诊所做“光氧动力”治疗。回北京的第三天,开车去看他,找了好一阵,终于在八达岭高速进京路段,找到了那个不起眼的诊所。好在唐旭的姐姐早早地在门口来等我,否则,我还真的不知道大门开于何处。
进了病房,发现房间的暖气还可以,设施也还行,并不像它的外观那样简陋。姐姐告诉我说,唐旭暂时不能说话,因为口里含着一种绿色的含服液体药物,既不能马上吞下去,也不能马上吐出来,需要在嘴里含服一段时间。过了大约二十分钟,药物时间过了,唐旭吞服了嘴里药物后,才开口讲话,说话的时候还能看到整个口腔全是发绿的液体。
我相信,那是一种很不好的感受。大约过了半小时,护士又来了,又把那个莫名其妙的嫩绿色液体打进唐旭的嘴巴里。
十二月上旬,我从深圳再次打电话询问情况时,唐旭告诉我说,那个做光氧动力治疗的医院从昌平搬到了贵阳,他们随即去了贵阳。
十二月下旬,我回北京过元旦节,唐旭住在北京佑安医院,我去看了他,这一次去看,心情很沉重,因为唐旭的病情显然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我去的时候,只有唐旭的女儿在病房里,当护理人员从外面推唐旭进来时,唐旭异样地对着我一笑。我的心不禁一阵痉挛:唐旭是用一种似曾相识的眼神看着我笑的!
“侯叔叔来看你了”。女儿强调了我的到来。
“从深圳回来了?”唐旭问我,这句话似乎又表示唐旭是正常的。
“是啊,回来过元旦节。”
在我和女儿说话期间,唐旭两次找他的电话。女儿回答她爸爸说:
“电话在的”。
“我的电话为什么在你哪里呢?“
显然,唐旭已经言不达意了,大脑所想的问题与行为之间会出现间歇性的不关联现象。因为,自从唐旭下肢不能动弹后,电话一直都是由家人帮他拿着。我知道这不是个好兆头,因为在人的整个身体器官中,治疗器械、药物等最难达到的地方就人的脑部了,一旦大脑有癌细胞侵蚀,就意味着治疗的难度会成倍的增加。
二零一一年一月五日,唐旭从北京佑安医院出院,在离家近一点的宣武医院做赫磁检查。那几天,几乎每天跟唐旭的夫人通话,十二日这一天,唐旭夫人告诉我,打算将唐旭送301医院(陆军总院),准备着去做脑部整体放疗。
十五日,我和我夫人去301医院急诊科的抢救室看望唐旭,此时的唐旭,已完全处于昏迷状态。我摸摸他的头部,他只能勉强地把眼睛睁开,茫然地看我一眼,接着又进入昏迷状态。
抢救室只是一个临时安排,条件很差,主要是太拥挤。没有想到的是,作为我们国家的顶级医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过道上挤满了看病的人,从门口经过挂号大厅进抢救室时,需要蛇行而过,而在抢救病房里,几乎挤满了病人和病人家属。
看到那种情况,真的很让人焦虑。唐旭夫人忙着治疗方面的事,我和我夫人守在唐旭的病床前,唐旭的呼吸已经很沉浊,插在唐旭身上的那些连着监视器的管子,会因为唐旭无意识地动弹而脱落,一旦脱落,监测仪器就会响起,那种环境下的那种响声,在感觉上几乎就是生命危险信号的直接说明,所以,我和我的夫人不停地要帮唐旭连上那些夹子样的器械。说真的,看到这种情形,我的担心逐渐开始在心里沉积。
住进去的前两天,暴露出来的问题很有些让唐旭夫人手足无措,一方面肿瘤科认为,唐旭现在的情况是脑部出血,压迫脑部神经而形成昏迷状态,如果不解决脑部神经恢复正常的问题,就达不到放疗条件,进了肿瘤科也没有任何意义。而另一方面呢,神经科又认为,是因为肿瘤的原因造成的神经压迫,如果不解决肿瘤形成的颅内高压问题,神经科也将是束手无策。
唐旭怎么能在如此尴尬的环境下长时间呆下去呢?而且在这个尴尬的环境里,护理起来也非常有难度。跟唐旭夫人讨论了一下:一种选择是,一定要找到熟人,通过关系,尽快进入正式病房。另一种选择是,如果301医院的正式病房实在进不去,那就退而求其次,转到比301医院低一个等次的其它医院,但前提是:直接进入病房,进入治疗状态。
事实上,从我进入急诊科的抢救室,第一眼看到病床上昏迷中的唐旭时,我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不祥的预感促成了我有一种直观的想法,那就是:在唐旭去之前,一定要到病房里去,不能在如此尴尬的环境下离开人世。
十七日,也就是在急诊室住了近五天后,唐旭住进了肿瘤科病房。那几天,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我坚持每天去看唐旭,有时候是约上几个博士同学一块去,有时候是我一个人去。唐旭的嫂子和姐姐已经分别从四川和重庆赶来了,好在已经进入正式病房,护理条件可以告慰唐旭身边的亲人。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我要回云南学校有事,然后就转道去遵义与我九十五岁高龄的老娘一块过春节。走的前一天,我最后一次去看唐旭,唐旭的情况仍然不好,虽然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但是从他的眼神和一种没有任何情感内涵的微笑,我深知,他对发生在他身边的一切,已经失去了思维能力。他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已经无法再储存进他曾经很丰富的亲情世界里了。
姐姐还在不停地用棉签从唐旭的嘴里清洗唐旭已经无力自主向外喷吐的浓痰,脸上时而会闪现出一种微笑,用那种亲人们期望是唐旭是唐旭内心真实的眼神,看着距离很近的亲姐姐,但是,我知道,那种不包含情感的机械式的微笑和仿佛是专注的眼神,显示的却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病态。
我告别了唐旭的嫂子和姐姐,同时也跟唐旭夫人说:如果不出意外,我可能要到春节后初十左右才能回到北京,那时我再来看唐旭。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我已在内心里感知:这可能已经只是一种美好愿望了。之所以言不由衷,只是不想将这种残酷的人生事实,直接表达出来,让唐旭夫人难过伤心而已。
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我在遵义老家,同时接到了唐旭夫人和徐风雷(师弟)的短信:唐旭已然仙逝而去。
唐旭的英年早逝,对于他所工作过的那个环境里的所有人,应该是一种莫大的惋惜,因为,像他那样纯正的为官者,像他那样谦逊的学者,在当今社会中已经少之又少了。
唐旭的英年早逝,对于他身边的所有亲人,对于像我这样与之交往很深的同学和朋友,必然是一种巨大的痛失,因为,像他那样具有厚待亲情,礼遇朋友,真实无欺品格的人,无论如何也不应该遭此不公的生命待遇。
既然唐旭已去,我也就没有必要急着赶回北京了,我相信,无论是以唐旭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还是他身边被他优秀做人品质所感动的朋友,都是会尽心帮着唐旭夫人处理他去后的种种事务的。更何况我已早就远离那种人喧人哗的俗世忙碌环境,也不太愿意再去参与其中了。问了一下唐旭夫人有关唐旭的后事安排,表达了我不能参加唐旭追悼会的意思后,我直接从贵州去了深圳。
在深圳,了结一些俗务后,于二月十八日回到北京。
与唐旭夫人约定了时间,二月二十日,我开车和她一块去八宝山公墓,办理上墓墙殡葬唐旭的相关事宜。咨询完了相关问题后,再次约定于十天后,正式去殡仪馆迎接唐旭的骨灰到八宝山做暂时存放。这期间,需要完成两件事情:一个是如何在唐旭的那块面积不大的墓碑上,写一段既能客观概括唐旭本人,同时又能表达追思之情的文字,二是由于八宝山公墓的暂存时间最长是四十五天,所以,必须在暂存最后期限前,将唐旭从临时骨灰堂里接出来,正式安放在确定的公墓位置上。
唐旭夫人给我看了那段墓志铭一样的文字,唐旭夫人自己的文化底蕴并不浅,加上唐旭有一个学历史的兄长,语法自然不是问题。在我看来,关键的问题是:能否从生命的角度,真实地反映唐旭的情感和人生意志。不过转念一想,毕竟,这应该是唐旭家人的事,所以,我看了后也不便提任何自己的想法,文字就这么确定了,需要尽快交给公墓方送到天津烧制。
数天后,还是我开车,唐旭夫人和唐旭的侄儿和我,我们三个人一块去殡仪馆迎接唐旭的骨灰。在八宝山殡仪馆,我经历了一场本来只属于唐旭家人才有的迎接骨灰仪式,就如我写在我四月十八日和我夫人一起去八宝山看唐旭时,站在唐旭墓碑前所回忆的那一幕。
送唐旭夫人去301医院处理唐旭住院期间的一些遗留事务后,我告诉了唐旭夫人,三月二十日左右,我要回昆明去上课,所以,唐旭的骨灰安放仪式我就不能参加了。
这样下来,涉及唐旭乘鹤西去后的所有正式场合,如追悼会、骨灰安放仪式等,我都没有参加,一方面,似乎都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而另一方面,也正合了我事前已抱定的想法,那就是:不参加所有由官方或其它正式方式为唐旭举行的公众祭典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