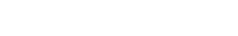Education with no regret : we have done the best
文 /厉以宁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五道口)81级毕业生厉放在其新书《旅行—与孩子共享的梦》一书的题记中写道: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我孩子的外公80岁寿辰。感谢他培养了我追求自由,热爱旅行的“性格”。在没有迁徙自由、思想禁锢、精神苦闷、文化单调和物质馈乏的年代,他为我订阅《地理知识》和《旅行家》杂志,让我看到“现实”生活以外的世界,开阔了我的眼界和胸怀,从小立志要自由自在地行走,自由自在地飞翔。
同时,感谢我的母亲,在省吃俭用的年代,她送给我第一部属于我的照相机;又在数码相机依旧昂贵的初始阶段,送给我第一部数码相机。让我把旅行的记忆留下,变成一本又一本的照片珍藏。生命的延续不仅是血脉的继承,更有精神的承传。我的孩子已经开始了他的旅程……本文为厉以宁先生为女儿的新书所做的序言,文字有形,父爱无声。
一
当厉放把这本书的打印稿放在我书桌上时,只说了一句话:“帮我写篇序言吧!”我一翻,这是一本散文集,也是一本游记,同她的上一本书《行走在欧罗巴的苍穹下》一样。我对她说:“上一本书我不是也没有写序言么?不也正式出版了,还博得好评呐!这本书的序言,我就不写了。”厉放一听就急了,紧接着说:“正因为您上一本没有写序,这本书的序言您一定要写。”尽管厉放已经离家多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后一直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工作,但在父母面前仍然保持了任性的本性。那就只好替她写序了。
厉放从小喜欢文学,一有空,就从我的书架上找出唐诗宋词之类的书籍阅读。小时候给她一点零用钱、压岁钱,积攒起来就买中外名著(小说),作为自己的家底,书上还写上“厉放藏书”几个字。但去农村插队,却改变了她人生的经历。插队回来后,经过努力,她最终转入金融学。她在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讲授过计算机课程,在香港岭南大学(当时叫岭南学院)当过经济学讲师。她在国内拿到货币银行学硕士,又在日本拿到公共行政管理学硕士后,最终在澳大利亚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从她的学习经历和后来的工作经历来看,她应该是我的接班人。谁想到她从新世纪开始后不久,却回到中学生时代的爱好,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大了,专心致志地写散文,写游记,抒发自己的感情和理想,并且乐此不倦,真有些出乎我和她母亲的意料之外。
记得厉放小时候,我曾对她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都重要,但相形之下,行万里路更有用。”话虽这么说,但在那时,哪有万卷书可读?更没有万里路可走!我自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在资料室工作,书是有读的,但行万里路的机会却轮不到我。我曾经在北京门头沟区西斋堂村下放劳动1年(1958年),在湖北荆州市江陵滩桥参加农村“四清”1年(19641965),在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州农场劳动两年(19691971),只此而已。这叫什么“行万里路”?厉放也是这样,从小在北京长大,跟着我们下放到江西鲤鱼州,后来又到北京郊区农村插队,这也不能叫“行万里路”。所以,必须先有可以“行万里路”的大环境,才能“行万里路”,才能从“行万里路”中得到收获。“读万卷书”不也一样么?“不必读书”或“无书可读”的日子我们不也经历过么?读书必须让读者有选择权,这是前提。如果既没有读书的选择权,又没有可读之书,“读万卷书”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改革开放使“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逐渐成为可能。厉放这一年20岁了,她赶上了好时候。当我为她写本书序言时,我不由自主地为她高兴:要不是改革开放,小时候所梦想的“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又怎能实现呢?又怎能亲自体验到“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加实用,更有意义呢?
二
写游记,不单纯是写些到过什么地方,那里有什么名胜古迹,出过什么样的名人,或者把风土人情描述一番。这样的游记是比较容易写成的,但读完后,除了增加一些知识、掌故之外,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游记的最大特点应当让读者有所回味,联想翩翩。这正是游记难写之处。
厉放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是我从字里行间所能看出来的。要让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并且回味无穷,不仅是文字技巧问题,更重要的在于有思想,有感情,还要有意境。历史是不可能倒转的,已经逝去的永远逝去了,人们可以回忆当年,但不能仅限于回忆当年,回忆应当更有益于对未来的展望。一件不经意的琐事,可能会勾起无尽的设想。这才是人生。仅仅生活于回忆中的人,至多是时代的匆匆过客,而不可能真正握住时代的脉搏。因此,我常对学生说,写游记不等于写回忆录,而更像是写随笔,因为随笔如果缺少思想,那就称不上是随笔了。当然,即使是写回忆录,也应该蕴涵着思想,随时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供读者深思。
然而,游记毕竟是游记。在游记中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只能是含蓄的,要结合情景而抒发,而不能像写随笔那样,或者像写回忆录那样,把要说的话直接倾吐出来。这正是难点所在。我感到厉放在考虑这一点之后,在用笔方面是下了工夫的。写游记,既要顾及思想性,又要顾及可读性和趣味性,三者缺一不可。一本被读者喜爱的游记,肯定是兼顾了思想性、可读性和趣味性等多个方面。
三
厉放这本游记,写的是他们一家三人的事情。这是一个典型的中西合璧的小家庭。孩子无疑是这个小家庭的核心。许多次旅游是因为答允了孩子的请求而成行的。他们把这看成是让孩子增长见识的机会。
孩子从小由他的父母带大。从4岁起,每年两次来内地。一次是放暑假,我们带他到国内走走;一次是春节期间,也就是放寒假时,我们和厉放、厉伟全家团聚。至今已经十几年了,一直如此。孩子从小懂得如何省钱,节约开支。有一次,他要从香港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去看母亲(厉放当时在那里工作),从香港乘飞机到韩国,再换机飞阿姆斯特丹。父子俩在韩国首尔机场内等待了11个小时以上。我们打电话问他:“香港不是有直达荷兰的航班吗?为什么要绕道韩国转飞机,还要在首尔待这么久?”孩子在电话里说:“外公,外婆,这样可以节省一大笔路费呐!”我和他外婆都笑了,说:“小学还没毕业,就知道省钱了。”
在同孩子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在了解了厉放和她的丈夫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之后,我感到实际上存在两种教育方式:一是“望子成龙式”的教育,另一种是“盼子幸福式”的教育。国内许多家长实行的是“望子成龙式”的教育,即总希望孩子在受幼儿园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的时间内能出人头地,最好能有什么特长,这样就能在中考、高考中名列前茅,最终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家长全部精神都在关注这一点,以便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使自己的孩子能顺利通过一关又一关。这就是“望子成龙式”教育。结果,不少孩子都是时间排得满满的,功课压得重重的,几乎透不过气来。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我所看到的则是:大多数家长对待子女采取“盼子幸福式”教育。“盼子幸福”不一定就是对子女放任不管,也不一定就是娇惯、溺爱子女,唯恐子女“不幸福”,而同样是教育孩子从小要走正道,要学会同其他同学友好相处,要关心别人,爱护环境,善待动物,节约物资等等。他们不像国内许多家庭,把家庭作业布置得很多,使孩子总有做不完的功课;也不像国内许多家庭那样,让孩子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上这个补习班,上那个补习班。
这就是“望子成龙式”教育和“盼子幸福式”教育的区别。厉放夫妇对待自己的儿子,可以归入“盼子幸福式”的教育一类。他们带孩子到世界各地旅游,经常是“寓教育于旅游之中”。孩子从小养成守纪律,乐于助人,爱护环境等好习惯。孩子喜欢潜水、驾帆船等运动,就让他去学习,去接受培训。孩子把零用钱捐给了慈善事业,他们从不干预。孩子将来学什么专业,考什么大学,家长只提一些参考意见,但主要是听从他自己的选择。这是和我们当初对待厉放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方式。有时我想,的确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不适用以当年我们教育厉放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小外孙了。
我相信,读者们在读完本书,尤其是书里提到厉放的孩子的成长过程时,对此一定会有所体会。
当然,我们夫妇对于从小严管儿女的做法,至今一点也不后悔。我们承认,当年对于厉放姐弟的教育是十分严厉的,但在那种情况下完全必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中,只有家教严格,在以后如此激烈的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竞争中,才能使他们在拼搏中取得优异成绩。直到他们两人顺利地完成研究生学业之后,我们才感到松了一口气—我们尽到了自己的力量。
今天,情况已经不同于过去。“望子成龙式”的教育正在被“盼子幸福式”的教育陆续替代。但愿我们的孙辈不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被做不完的学校作业和家庭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来。
四
父亲给女儿的书写序,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确实如此,当我把过去这些年为厉放写的诗词选出一些再仔细阅读的时候,往事历历在目,仿佛过去还不太久,尽管那至少也是中年以前的事了,有些诗词甚至是40多年前写的。
收集在《厉以宁诗词选集》(上、下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出版)中关于厉放的最早一首词写于1962 年,当时厉放三岁半。
南乡子
记厉放患麻疹并发肺炎,何玉春连夜自辽宁鞍山赶回北京(1962年)
急电促回京,
仆仆风尘两地行,
未进家门先缓步,
轻轻,
小女今宵怕受惊。
淡月照中庭,
最贵人间母子情,
彻夜披衣床角坐,
天明,
再测高烧可退清。
接下来就是1967年,厉放上小学了。当时我们家住海淀太平庄,厉放就近在街道小学读书。
木兰花
送厉放上小学
红绸辫结迎风舞,
雪白衬衣新绿裤,
邻家小女伴随行,
袅袅歌声墙外路。
聪明莫被聪明误,
招手遥呼重嘱咐,
花开温室怯春寒,
知否高山松柏树?
1977年厉放高中毕业,下农村插队。
调笑令
送厉放到昌平马池口村插队
(1977年)
飞雪,
飞雪,
大地生机未绝。
且看三月春晴,
又是满山草青。
青草,
青草,
雪后成长更俏。
厉放插队归来,刻苦学习,终于在1985年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获得硕士学位。
鹧鸪天
为厉放获得硕士学位作
(1985年)
数载坎坷志未消,
登山且莫问山高,
野无人迹非无路,
村有溪流必有桥。
风飒飒,路迢迢,
但凭年少与勤劳,
倾听江下涛声急,
一代新潮接旧潮。
1998年,厉放在澳大利亚莫纳石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为此,我填了一首“减字木兰花”。
减字木兰花
贺厉放获得博士学位
(1998年)
艰辛历尽,
风雨当年凭自信。
更上层楼,
莫让时光似水流。
扬鞭再赶,
创业从来无早晚。
处世唯谦,
天外须知还有天。
到了2003年11月,我们夫妇从高雄飞抵香港。厉放全家住在香港,儿子一家也自深圳到达香港团聚。他们姐弟都是11月出生。为祝贺厉放45岁,厉伟40岁生日,我赠给他们一首“洞仙歌”。
洞仙歌
为厉放四十五岁,厉伟四十岁作
(2003年)
弟顽姐护,
幼时情难表,
陋巷危房度年少。
浪中游、不问前站遥遥,
惊回首,
往事如今缥缈。
南国花未谢,
碧海青山,
云下烟波接芳草。
暮雨正潇潇,
桥跨罗湖,
秋凉去、香江春早。
课子女,
日夜识辛劳,
念父母当初,
掌灯严教。
这几首词让我们夫妇回想起很多往事。有些事,当时觉得很艰辛,但正如登山一样,越过了峰顶也就不再介意了。回忆依旧美好,在为厉放写序言时,我想起了这几首词,就一并附上。
(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旅行—与孩子共享的梦》一书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在2010年10月出版。)